《货币金融评论》2020年第7-8期.pdf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大国金融化的逻辑 张成思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摘要:经济金融化问题备受各界关注。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现代金融学等各流派对 金融化逻辑的意见分歧很大,并展开了激烈而又长久的论战,导致各界对金融化的概念、属性、驱动因 素及其逻辑内涵等重要问题的理解不但没有更清晰,反而日益模糊,这给决策层的现实判断也带来了极 大困扰。本文基于宏微中观三个层次阐释大国金融化的逻辑,指出宏观金融发展说和微观金融市场说推 动了泛金融业的金融化,并且影响了微观企业的经营理念,再加之实践中企业趋利避险,从而驱动了微 观企业的金融化;而宏微观层次的金融化也微妙地催生了中观层次普通商品的金融化。三个层次的金融 化本质上都反映了资本的逐利天性,并从深层次反映出发展中大国对多元化金融体系日益增长的需求。 虽然过度金融化会带来负面冲击,增加大国经济的脆弱性,甚至可能引发危机,但是负面冲击是随机冲 击而不是系统性冲击,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矛盾的累积”甚至是“发展的陷阱”。正确认识和 理解金融化的深层次逻辑并包容资本的逐利天性,合理运用金融化理念可以推进多元化和市场化金融体 系发展,进而实现“好的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国计民生的目标。 关键词:金融化 金融发展 政治经济学 一、金融化的概念与界说 近年来,金融化问题正在成为货币金融领域的一个前瞻性研究主题,而且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 学交织,成为一个备受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金融化的内涵颇为丰富,不同层次的金融化问题具有 迥异的理论和现实逻辑,对金融化及其逻辑进行深层次阐释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各界对“金融化” 的定义较为宽泛和模糊,一般沿用西方学界的研究界说,用金融化来表示金融对经济领域的渗透和 主导,大致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从宏观视角定义的金融化概念,大体上可以归纳为“金 1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融的发展”、“泛金融业的膨胀”或“泛金融业的金融化”,即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部门中的相对 比例上升(如产出占比、利润占比等);从微观视角定义的金融化,本质上可以概括为“微观企业 的金融化”,即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资占比及金融渠道获利占比的不断提升。事实上,除了以上两 个层面,还有一个语义更为模糊的中观层次的金融化问题,即“商品金融化”,既包括流行于西方 学界的“大宗商品的证券化”(commodity securitization),又包含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普通商品金 融化”(goods financialization)。 从宏观层面开展的金融化研究,基于价值观判断和研究范式特征,又可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分 1 支 。第一个分支可以概括为新古典经济学派,他们所说的“金融深化”、“金融发展”和“金融增 长”等表述,本质上就是与金融化紧密相关的内容。例如,Gurley 和 Shaw(1955)提出经济发展的 金融视角,之后 Patrick(1966)对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研究、McKinnon(1973)对货币与资本的 分析和 Shaw(1973)的金融深化说在上世纪 60-70 年代就颇有影响,而 King 和 Levine(1993)和 Rajan 和 Zingales(1998)的重要文献进一步升华了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理论,本质上都是金融化学 说的内容;事实上,Goldsmith(1969)提出的金融结构分析方法也可以视为金融化学说的前身和渊 源,而更早的文献甚至可以回溯到熊彼特的经济发展说(即 Schumpeter,1911)。 从理论逻辑上看,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与新近的金融化学说一脉相承,但是前者的价值观强调 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后者的价值观基础则是金融过度膨胀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在以 上提及的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文献中,一部分讨论金融深化与宏观经济发展的关系,另一部分则关 注金融领域的结构性变化,提出金融发展即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工具的增多、金融机构服务领 域的扩大和功能的增强以及金融结构朝向高端的演进,这些实际上也是金融化的特征。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期刊在 2013 年第 2 期刊登了一个“金融部门大增长”的专栏(共 5 篇文章), 分别从金融资产管理费用(Malkiel,2013;Greenwood 和 Scharfstein,2013)、金融功能(Cochrane, 2013)、算法交易(Kirilenko 和 Lo,2013)以及金融发展与真实经济增长关系(Philippon 和 Reshef, 2013)角度研究金融增长问题,实质上就是阐释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宏观层面的金融化问题,这 些讨论的价值观基础则更加折中一些。从一定程度上看,金融发展和金融化更多是一个事物在不同 阶段的表现。在相对早期,如果金融部门的发展程度不足以匹配宏观经济的规模和对金融服务的需 求,经济中需要金融部门帮助克服的摩擦较多,则金融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较大。如果金融部门 1 对于流派划分,本文总体上依据不同研究流派对“金融化”的价值观判断、研究范式特征,并参考相关研究所发表 期刊的名称和定位(aims & scope) 。各流派价值观判断和研究范式特征也与各自所发展和盛行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而且 本文划分的流派(文献群)彼此之间还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虽然本质上讨论的主题都是金融化但不同分支的文献之间几 乎很少互相引用,这也是作者在对流派进行划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2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过度发展,产生了比较大的挤出效应,那过大的金融部门本身就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摩擦,此时就会 引发对于金融化的担忧。 宏观视角的另一派别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和激进政治经济学2,Crotty(1990; 2005)、Arrighi(1994;2003)、Amin(1996;2003)和 Harvey(2005)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 更早还可以追溯到马克思《资本论》、希法亭《金融资本》以及列宁对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论述, 我们可以将之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流派。这一派与新古典经济学派不同,他们频繁地使用 “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这个表述,用以形容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态,并且将金融化与全球化和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联系起来,认为金融化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一唱一和,构成了全球资 本主义新框架,在全球范围内都带来了破坏性影响。显然,这一流派或多或少地戴上了有色眼镜审 视金融化问题,不厌其烦地将金融化与“脆弱性”和“金融危机”等负面表述放在一起,这一点可 以从美国麻省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杰拉德·爱普斯丁主编的《金融化与世界经济》一书中 窥见一斑(Epstein,2005)。在这些文献中,给金融化的宏观定义是“金融力量、金融机构与市场 以及金融行业的工作者在全球经济运行中扮演着越来越多的角色”。注意,这一定义中对金融角色 的修饰语用的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重要”。因此,这一概念简言之就是金融行业的扩张 与膨胀。Orhangazi(2008)认为这一流派界定的金融化是资本主义长周期中最近的一个典型特征。 从微观角度定义“金融化”,主要是基于微观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例如,“企业利润的积累日 益倚靠金融渠道而不是传统的贸易和商品生产”(Krippner,2005),“非金融企业卷入金融市场” (Stockhammer,2004;Stockhammer 和 Grafl,2010),以及“各种经济行为的核心从生产部门和一 些外延的服务部门变为金融部门”(Foster,2007)。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源于 金融实务以及金融体系发展对公司治理股东价值论的影响(如 Froud 等,2000)。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西方资本市场的大发展带来了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诉求,从而改变了非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 理念,即由追求长期增长转变为追求短期内的股东价值最大化,表现为非金融企业将利润分派给股 东而减少生产性投资。这样,企业的发展就严重依赖于其在金融市场的表现,企业更加侧重市值管 理、股权运营(如并购、抵押)等金融行为,企业利润的积累也就自然越来越多地从金融渠道获得。 Lazonick 和 O‟Sullivan(2000)将这种转变概括为企业“缩小规模、增大分派”的模式,而这种转变 2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流派的划分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对金融化的价值观判断明确是负面的,二是研究范式的 意 识 形 态 特 色 非 常 明 显 , 马 克 思 主 义 、 资 本 主 义 、 金 融 资 本 主 义 ( financial capitalism ) 甚 至 金 融 帝 国 主 义 (financialimperialism)等概念充斥于这些文献,而且这些文献所发表的期刊名称一般都带有政治经济学、左翼、后凯恩斯 等意识形态特征明显的表述(当然,期刊名称没有意识形态特征的学术期刊所刊登的文章也可能是有意识形态的,只是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表现更加显性和突出) 。另外,因为左翼(左派)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称为激进政治经济学, 都是以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者的形象出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并批判传统经济学的学说,所以本文将西方马克思主 义、激进政治经济学以及左翼政治经济学等都归类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3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带来了“券池资本主义”(见 Froud 等,2002;Van Treeck,2009),本质上说的就是本文此处所讨 论的微观企业金融化问题。 从经验证据看,微观企业金融化逐渐成为世界范围的现象,只不过在发达国家出现得更早一些。 例如,美国非金融企业自 1970 年就开始出现了金融化趋势,80 年代中后期金融化达到一个顶峰阶 段(见 Krippner,2005);阿根廷、墨西哥和土耳其这三个新兴市场国家则在 90 年代后期出现明显 的微观企业金融化现象(见 Demir,2009a,2009b);中国的微观企业自 2006 年以来也出现了明显 的金融化特征(见张成思和张步昙,2016)。微观企业金融化不仅会导致全社会实物资产的积累大 大减慢(Stockhammer,2004),而且可能会造成实业投资率下降(这是否是各国普遍现象还存在争 议;见 Kliman 和 Williams,2015)。 对比以上宏微观金融化的研究内容可以看出,宏观层面的金融化主要是指金融深化或者金融发 展,而微观层面的金融化则更多关注企业降低在实体经济的投入、参与或主导微观金融活动的行为。 尤其是参与金融活动这一微观概念,与宏观理论中的金融部门、金融体系发挥更大作用似乎是两个 概念,但是本质上仍然具有内在联系。企业的诸多金融活动(金融投资和融资活动)一方面是通过 宏观金融体系实施的,另一方面企业金融活动的主体部门(其财务部门或者财务公司)也是现代金 融体系的一部分(在我国金融机构编码中为 C 银行业存款类)。因此,企业层面的微观金融化与宏 观层面的金融化实际上具有内在融合、深度关联的特性。 另外,尽管从宏微观视角定义金融化的具体内容有所差别,但对金融化过程中的特征事实具有 以下几点共识:第一,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大幅提升,从事金融服务的企业在经济、 社会和政治中的重要性增强了;第二,非金融企业日渐卷入金融活动,将收入从产业部门转移到金 融部门;第三,宏微观金融化都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而且使得国民收入中劳动份额降低,公司 高管薪酬提升,劳动者收入的差异扩大。 从中观视角定义金融化,主要是指具体的资产或大宗商品的金融化,这一定义更加侧重资产或 产品的金融属性和金融市场的功能。不难看出,资产或大宗商品金融化的一端连接微观企业或者机 构投资者,另一端则连接着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因此可以视为中观视角的金融化。在资产金融化 方面,有研究认为(如 Chen 等,2013),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日益增多的各类资产(特别是 期货资产)都被转化为金融资产,从本质上说,金融化就是改变资产的流动性高低。不过,中观层 次的金融化更多的是基于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问题进行研究。例如,Tang 和 Xiong(2012)指出, 最近十年来各种大宗商品价格同步波动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争论,一派将原因归于简单的宏观经济 因素(例如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当短期内供给不足而需求过多时就会出现暴涨,在遇到经济形势 4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急转直下时又暴跌。另一派则认为由于有大量的投资进入商品期货市场,导致价格形成机制被扭曲, 根源是指数投资者的增加。 2000 年之前,尽管期货合约在许多大宗产品上使用,但是商品期货价格与典型金融资产价格的 变化特征并不相符。例如,商品价格与股票没有同步性(Gorton 和 Rouwenhorst,2006),相互之间 也没有同步性(Erb 和 Harvey,2006)。这些都与典型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化截然不同。这种差异 意味着商品期货市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与所谓的外部“金融市场”(证券市场)以及相互之 间都缺乏关联。而当资金涌入商品期货指数时,商品期货市场出现“金融化”的过程,即商品期货 价格与典型金融资产的关联性增强,且不同商品期货价格波动彼此关联。由于产生了金融化过程, 大宗商品价格不再简单地由它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来决定,而是被各种金融因素所主导。 不难看出,以上所述各种不同层面对“金融化”的界定,主要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实践,从相 当程度上反映了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背景下学界对“金融化”逻辑的理解。我们知道,以美国为 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自 1970 年代之后开始放松金融管制,金融行业迅速扩张,各类金融市场在国家经 济中的地位和威力都得到了迅猛发展。 然而,学界对经济和商贸快速发展的中国出现的普通商品金融化情况有所忽视。中国与美国的 发展阶段不同,金融市场格局也不尽相同,美国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而我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 体系。从一定程度上说,在中国,拥有货币资本或者获得信贷资源才更能具备将商品进行“金融化” 的条件;而在美国则是非银行金融市场主导金融化进程,中观层次金融化现象更多体现在金融产品 过度衍生化方面(如大宗商品金融化、金融产品多重证券化),这与中国存在本质区别。近年来, 中国商品市场上出现的葱姜蒜等普通商品价格大幅波动是普通商品金融化的典型案例(张成思等, 2014),这些普通商品金融化现象表征了特定区域或者特定时域内经济金融发展的典型特征,但却 并未受到金融化领域研究的重视。而以往学界所关注的商品金融化实际上是大宗商品期货指数投资 规模的增加趋势等基于金融市场的大宗商品金融化(commodity financialization)和资产证券化(如 Tang 和 Xiong,2012;Basak 和 Pavlova,2016),本质上是金融市场交易行为,交易标的物是金融产 品(如期货指数);而中国的普通商品金融化是商品市场的金融化现象(goods financialization),标 的物是普通商品而不是金融产品。 综上所述,“金融化”既不局限于宏观层面金融的发展与泛金融业的膨胀,也不仅仅只是微观 层面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或者中观层面发达经济体的期货市场上大宗商品的证券化;“金融化” 既涵盖以上层次,又包含近年来出现的普通商品金融化。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普通商品金融化与大 宗商品金融化所发生的市场层次并不相同(前者是商品市场而后者是金融市场),但是金融化机制 极为相似(因此都可以归结到中观层次金融化):大宗商品金融化是在大宗商品投资的受欢迎程度 5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急剧上升的背景下, 引发的前所未有的机构资金流入商品期货市场;而普通商品金融化则是在部分 普通商品投资的受欢迎程度大幅上升的背景下, 引发机构和个人资金流入普通商品市场的现象。 从金融化三个层次发生的国别主体来看,美国是发达国家的代表,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从经济规模(如 GDP)、人口规模以及金融市场规模等指标综合来看,前者是最大的发达国家,而 后者则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本文研究的主题可以称为“大国”金融化的逻辑。注意,本文 所谓的大国,其涵义既抽象又具体,抽象在于其不局限于中国和美国,具体在于我们可以对号入座 到中国和美国,并且不排斥其他国家。从表 1 给出的二十国集团(G20)国家的经济规模、金融市 场规模和人口规模等具体指标来看(基于 2017 年数据),中国和美国仍然在诸多方面占据了世界主 要国家前列,因此二者可以视为大国的代表。 表 1. G20 集团国家的产出、货币化程度以及金融规模等指标(2017 年度) 美国 中国 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 印度 巴西 意大利 加拿大 俄罗斯 韩国 澳大利亚 墨西哥 印度尼西 亚 土耳其 沙特阿拉 伯 阿根廷 南非 名义 GDP (十亿美 元) 19390.60 12237.70 4872.14 3677.44 2622.43 2582.50 2274.22 2055.51 1934.80 1653.04 1577.52 1530.75 1323.42 1150.89 32120.70 8711.27 6222.83 2262.22 3917.90 2749.31 2331.56 954.72 587.31 2367.06 623.42 1771.77 1508.46 417.02 股票市值 /GDP (%) 165.65 71.18 127.72 61.52 149.40 106.46 89.65 46.45 27.29 143.19 39.52 115.75 113.98 36.23 人口规 模 (亿) 3.26 13.86 1.27 0.83 0.66 0.67 13.39 2.09 0.61 0.37 1.44 0.51 0.25 1.29 领土面积 (万平方 公里) 914.74 938.82 36.46 34.94 24.19 54.76 297.32 835.81 29.41 909.35 1637.69 9.75 769.20 194.40 46.97 520.69 51.27 2.64 181.16 54.33 80.84 227.51 26.72 0.82 76.96 686.74 70.29 38.89 451.38 65.73 0.33 214.97 637.43 348.87 28.71 72.21 39.25 180.54 108.74 1230.98 17.06 352.85 0.44 0.57 273.67 121.31 M2/GDP (%) 信贷/GDP (%) 金融市场规模 (十亿美元) 90.28 202.60 242.38 90.00 148.48 79.93 75.68 99.18 89.64 106.40 59.09 146.23 116.84 38.79 241.89 215.24 346.65 128.59 167.51 157.67 73.46 111.26 166.16 172.33 58.85 170.06 182.77 55.17 1015.54 39.88 851.55 说明:本表报告了 G20 国家的相应指标,以 2017 年度数据为基础计算,原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其中领土面积指 陆地面积)。G20 由九国集团(中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和十个重要新兴工业 国家(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以及欧盟组成。廿国 集团的 GDP 总量约占世界的 85%,人口约 40 亿。 6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为什么研究大国的金融化逻辑更有价值?原因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大国的金融市场高度 发达,其宏微中观各层次金融化演进过程比发展中国家更早,文献积累也更多;以中国为代表的发 展中大国则表现出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产品不丰富与货币化程度快速增长的矛盾,这一特征背景 下催生的金融化逻辑与发达大国的金融化逻辑既有沿袭性又有差异性,沿袭性表现为宏微观层次的 金融化特征,差异性表现为中观层次的普通商品金融化趋势(美国并不存在普通商品金融化特征)。 而与大国相比,“小国”在经济总量、市场规模、金融规模、货币化程度等方面的水平较低,尽管 也存在个别层面的金融化现象(如前文提及的拉美国家的微观企业金融化现象),但是由于经济规 模、市场容量等有限而制约了多层次金融化的发展,因此金融化特征既不具有多层次全面性,又不 具有典型特征。 因此,本文以大国(主要是中国)为研究主体,通过细致分析指出,大国金融化可以归纳为三 个层次,一是宏观层面的泛金融业金融化,二是微观层面的企业金融化,三是中观层面的商品金融 化,三个层次的金融化逻辑紧密联系又不尽相同,存在分歧又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与此对应, 本文定义的“金融化”逻辑有三层含义:一是泛金融行业快速发展并在经济社会层面逐渐占据主导 地位;二是实体企业(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积累越来越多地来源于金融渠道;三是普通商品交易机 制中金融的特质与日俱增,以至于普通商品的价格决定越来越脱离真实交易中的供求关系,取而代 之的是进入相应市场资金量的大小,商品不是作为商品在交易,而是把对这种商品的所有权作为一 种金融资产(商品则成为该金融资产对应的标的),购买目的是为了转售所有权获利而非使用商品 本身。基于下文分析可以看到,三个层次的金融化本质上都反映出资本逐利特性,并从深层次指向 发展中大国对多元化和市场化金融体系日益增长的需求。 二、泛金融业的金融化 泛金融行业的金融化,主要表现于金融部门相对于生产部门的日益扩张,即金融部门在国民经 济部门中的产出占比、利润占比以及吸纳就业占比的提升。上世纪 70 年代之后,发达国家在金融 市场结构转型、新科技变革以及监管理念变化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传统金融行业(即银行与证 券)、保险业与房地产业共同构成所谓的“泛金融部门”,并在此后快速发展,直至形成美国规模 最大的行业。根据这几个部门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泛金融行业被记为 FIRE。有数据表明,美国 金融业对 GDP 的贡献度在 1950 年为 3%左右,1980 年上升到近 5%,而 2006 年则达到 8%以上 (Greenwood 和 Scharfstein,2013);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传统生产行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 中的占比由 1950 年的 30%下滑到 2010 年的 10%。同时,Foster(2007)的研究指出,最近 20 年来泛 7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金融业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以及该行业的利润总规模等方面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泛金融 行业对美国 GDP 的贡献率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5%不断上升,在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一 度上升到超过 20%,同期的制造业对 GDP 的贡献度则日益下降,从 1980 年的 20%左右下降到 2007 年的 10%左右。Krippner(2005)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显然,经济活动的重心正在从生产行业转向金 融行业。 不仅美国如此,中国也存在类似的现象,甚至泛金融行业的膨胀情况比美国更加突出。具体来 说,我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A 股)及非上市公司计算了 2004-2018 年中国泛金融行业净利润占所 有公司净利润总额的比例(样本起点受非上市公司数据的可获性限制为 2004 年),同时计算了第二 产业和服务业(金融行业除外)的利润占比指标作为比较,结果归纳在图 1 中,其中上市公司的数 据基于 A 股上市公司年报,非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信用债发债企业财务分析报告。图 1 给出了强烈的 反差:泛金融行业的利润占比自 2004 年以来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而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和除金 融以外的服务业总体上表现出下降趋势,其中第二产业的下降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从具体数字来 看,泛金融行业的利润占比从 2004 年的 15%左右一路上升至 2018 年的 60%左右。如果将泛金融行 业的口径缩小为传统金融行业,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根据麦肯锡 2016 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的测算, 2016 年中国金融行业的经济利润占到中国经济整体经济利润的 80%以上。经济体利润越来越多地通 过金融渠道而非其他渠道获得,利润代表的资本积累明显地展示出中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 70 60 泛金融行业 第二产业 服务业(除金融) (%) 50 40 30 20 10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20 16 20 17 20 18 0 图 1 中国不同行业企业(上市&非上市)的利润占比时序图 原始数据来源:WIND 资讯数据库,经作者计算。图中数据基于有统计数据公布的中国上市和非上市公司数据,其中 上市公司的利润数据来源于 WIND 我国各行业上市公司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行业区分采用证监会 CSRC 分类方法, 其中 FIRE 行业包括 CSRC 金融业、CSRC 房地产业和 CSRC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非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 WIND 信用债发债 8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企业财务分析,包含金融和非金融企业,含有 2003-2018 年非上市企业共 57842 个观测值,利润数据采用净利润指标。具体 计算方式是用净利润除以总净利润。 中国金融行业的利润占比如此之高,究竟与金融业的竞争和效率等因素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 仍然是待解之谜,但是即使暂时不考虑竞争和效率与利润之间的确切关系,资本和经济利润高度集 中于金融行业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并无益处,这一点也是明确的。中国的这种金融化还意味着泛金融 行业在生产和就业结构中地位的提升。通过计算 1994 至 2018 年期间中国 FIRE 行业占 GDP 的比率 以及相应就业人数比例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看到(图 2),伴随泛金融行业的不断发展,其对 GDP 的贡献率、行业就业人数比例都在稳步增长。从具体数据来看,泛金融行业的 GDP 贡献率在过去 的 20 年从 9%上升到 15%左右,而 FIRE 行业的吸纳就业比例从 1994 年的 2.2%上升到 2018 年的 6% 左右。 图 2 同时还对比了中国与美国 FIRE 行业 GDP 贡献率与吸纳就业占比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到, 中国 FIRE 行业的 GDP 贡献率一直比美国低,但是差距在 2004 年之后开始逐渐缩小;而中国 FIRE 行业吸纳就业占比在 2015 年之后超过了美国同期水平。当然,中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如果以美 国倒推 20 年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大致可比的话(2018 年中国 FIRE 行业 GDP 贡献率 14%、吸 纳就业占比 6%,美国 1998 年则分别为 16%和 6%),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现阶段在这两个指标上 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20 7 中国FIRE行业GDP贡献率 美国FIRE行业GDP贡献率 18 (%) 6 16 (%) 中国FIRE行业吸纳就业占比 美国FIRE行业吸纳就业占比 5 14 4 12 3 10 20 18 20 16 20 14 20 12 20 10 20 08 20 06 20 04 20 02 20 00 19 98 19 96 19 94 20 18 20 16 20 14 20 12 20 10 20 08 20 06 20 04 20 02 20 00 19 98 2 19 96 19 94 8 图 2 中国和美国泛金融(FIRE)行业的 GDP 贡献率与吸纳就业比率(1994-2018) 原始数据来源:CEIC 数据库,经作者计算;FIRE 行业的产出包括传统金融行业、保险及房地产行业的产出;吸纳就 业是指各行业城镇就业人数。 对泛金融行业的金融化研究,并没有止步于金融部门的膨胀层面,而是进一步发展到金融部门 膨胀带来的高利润以及食利阶层(rentiers)财富与权势的扩张。所谓食利阶层,其实就是指拥有巨 额资产、靠利息便可生存的阶层,这些人倚靠金融资产回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这类人在我们国家 9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改革开放初期被称为“息爷”。食利阶层的典型特征就是依靠生息金融资产获得较高收入,这与依 靠生产经营而获得收入的模式形成鲜明反差。已有研究发现,最近 30 多年来,经合组织国家的食 利阶层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出现趋势性上升(Epstein 和 Jayadev,2005)。Hilferding(1910) 的研究表明,食利阶层的收入相对升高的现象早在 20 世纪初的金融化浪潮中就出现过,只不过由 于此后多次出现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等负面冲击,这种现象没有一直保持下去。然而,1980 年之后, 受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金融市场化转型蜕变影响,食利阶层的高收入现象似乎又出现了明显端倪。 最近的一些研究似乎印证了这一趋势,例如 Bonizzi(2014)的研究暗示,由于短期金融投资的高回 报,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资本积累以后成为食利阶层,造成收入差距的增大。 需要说明的是,金融部门膨胀之后的一个典型事实是社会生产更多地依靠金融资本,所以资本 持有者在产出分配中会获得更多收益(从标准的生产函数即能看出),与此对应的则是金融部门相 关阶层的财富和权势的上升,原因在于食利阶层掌控的资本不断增加之后,政治影响力也逐渐增加, 进而形成利益集团(Rajan 和 Zingales,2003),使得政府推出更利于这一阶层的政策,从而导致财 富和权势继续膨胀。当然,此处的价值判断主要是从文献研究的回顾角度出发,即从社会阶层财富 和力量变迁的角度来观察金融化问题。本文认为,金融部门膨胀带来高利润和财富与权势的膨胀只 是金融化的一个层面,并不能完全排斥经济与金融的发展,否则就不会有金融化的金融发展说。 相较于食利阶层财富的积累和增长,其权势的扩张不容易给出具体的度量指标。从与本文的相 关性角度说,股东价值论的兴起是食利阶层权势扩张与膨胀的特殊表现。也就是说,股东价值最大 化的理念从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企业决策理论。以往,公司治理追求的首要目标是市场的优势 地位,生产和经营性增长是公司治理的根本目的,获利并非主要目标。1970 年代之后西方兴起的股 东价值论,改变了公司治理的基本理念,将公司治理权的重心从企业核心管理层转到股权持有者手 中。在这一背景下,随着机构投资者的不断壮大,形成了资本主导企业行为的结果,宏观层面的金 融化渗透到微观企业层面,这一点与本文第三部分将要阐述的微观企业金融化存在着细致而又微妙 的联系。 泛金融业的金融化还包括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影子银行的定义并不严格,多用于刻画非银行 金融机构游离于常规监管法规的边界,从事一些与传统商业银行类似的业务。在本文看来,影子银 行的本质属于泛金融行业的金融化,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将金融化学说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注意, 影子银行的业务内容在发达国家市场和我国市场上的表现不尽相同,发达市场的影子银行主要反映 在资产证券化业务链条上,而我们国家的影子银行业务更多地是通过改换通道对金融资本进行转手 和搬运,本质上反映了金融行业扩张金融化行为的边界。因此,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本质上也是泛 金融行业金融化的重要表现。 10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另外,在泛金融行业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居民家庭部门也出现了典型的金融化现象,主要表现 为家庭部门的金融资产不断增加,同时也体现于家庭部门的金融负债日益活跃。一方面,居民家庭 部门金融资产占比不断增加,西方国家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居民参与股票市场或者 共同基金(Davis 和 Kim,2015),而我们国家居民金融资产主要是储蓄存款(占比超过 50%), 不过近年来其他类金融资产占比有所提升。另一方面,由于泛金融行业的大发展,带动金融机构 (特别是银行)将贷款对象转向家庭部门,例如国外早已盛行且国内也日渐盛行的居民消费贷款, 也有诸多研究证明新兴市场多个国家的银行部门越来越多地将贷款生意转向家庭部门,使得居民金 融负债不断增加(Bonizzi,2014)。家庭部门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日益增长,可以看成是泛金融 业金融化的延伸,更加凸显了泛金融业金融化的深远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流派看来,以上种种泛金融行业的金融化,无论是金融部门的膨胀、 食利阶层财富与权势的提升,还是影子银行与家庭部门金融化程度的提高,都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 资本主义新纪元的转变、经济与社会的系统转型以及金融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病态关系 (Lapavitsa,2013)。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流派认为泛金融业金融化的驱动逻辑是资 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这种金融化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破坏 性。 本文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带着完全批判的有色眼镜看待泛金融行业的金融化问 题略有偏颇。至少从金融运营对现代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角度看,应辩证看待金融行业的扩张与 膨胀(Van Treeck,2009)。更重要的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以及新自由主义思 潮本身并不具备外生驱动金融业扩张的能力,而且全球化驱动金融化的结论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Philippon 和 Reshef,2013)。事实上,最近二三十年以来泛金融业金融化的驱动逻辑,主要体现 于金融学领域(而非社会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3)两条平行发展的主线,一是金融发展和金融 深化学说的理论推动,二是现代金融学宏微观范式结构性转变的驱动4。 3 社会学对金融化问题的研究范式介于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不过也多是偏宏观层面的研究, 一方面对金融化的价值观判断基本是负面的,但是意识形态又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流派那么鲜明;另一方面社会学 领域对金融化的研究一般不强调经济学理论模型和计量分析,而强调经济的社会政治分析;而且,社会学领域的相关文献 所发表的期刊名称多与社会或社会学相关(如 Economy and Society,Socio-Economic Review) 。 4 关于现代金融学的范畴和发展,Miller(2000)认为,现代金融学可以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范式,二者的典型区别 在于研究范式是以理论分析为主还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Miller 将宏观范式形象地说成“经济系范式”(economic department approach) ,微观范式则被说成是商学院范式(business school approach) 。虽然 Miller(2000)提出了“现代金融学” (modernfinance)的说法,并且指出 1950 年代是现代金融学的起点,但是 Miller 所说的现代金融学主要是指 1950 年代之后 发展起来的微观金融学内容,因此确切地说应该是金融学的现代形式(finance in its modern form) 。从更全面的视角看,现代 金融学虽然强调 1950 年代的分水岭时点,但是并非专指 1950 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微观金融学,而是强调 1950 年代之后快 速发展的微观金融学与传统宏观金融学形成现代金融学两大支柱,宏微观金融学共同发展构成了比较完整、能够上升到学 科层次的现代金融学体系。也就是说,尽管 1950 年代以前宏观金融学理论(例如货币银行学)发展已久,但是无法独立 支撑一门学科,因此也就无从谈起“金融学”或“现代金融学” 。 11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首先,如果我们沿着主流的新古典学派金融发展说和金融深化说的研究按图索骥,可以推演出 泛金融行业扩张的理论基础。泛金融行业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各界对金融发 展说(即金融正向推动经济发展)的广泛认同。这种认同得益于金融发展学说代表性人物的影响和 研究推动。特别是戈登史密斯、麦金农和肖等关于金融正向推动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影响力巨大 (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Shaw,1973),加之后来又被诸多学术大家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和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之类的经济学顶级刊物加以推崇(如 King 和 Levine, 1993;Rajan 和 Zingales,1998),因此金融业扩张具备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尽管近年来有研究敏锐 地发现金融发展学说更适用于 1960-1989 年期间的数据而在此后的实证表现有弱化的迹象(如 Rousseau 和 Wachtel,2011),但是很难动摇过去三十年里各界对金融发展说的坚定信念。因此,金 融发展说在实践中被转化为大力发展金融业的现实行动,从而推动了泛金融行业在各个层面的扩张 和膨胀,而金融业的盈利性也日益表现为资本的逐利性。所以,金融发展说在一定程度上豢养了资 本逐利的天性。 其次,泛金融行业膨胀的另一个层面的驱动逻辑,在于现代金融学宏微观范式在 1952 年之后发 生的分水岭转变,即金融学的研究范式从宏观理论主导变为微观实践主导,这种转变极大地推动了 微观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实践发展,也就自然导致金融规模不断扩张,出现了金融行业的金融化。 这一历史性转变需要回溯到 1952 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哈里·马克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的横 空出世(Markowitz,1952)。根据诺奖得主默顿·米勒 1999 年在德国金融学会成立五周年纪念会上 的讲话(Miller,2000),马克维茨 1952 年投资组合理论的提出,是现代金融学的分水岭。这一理 论不仅激发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相关研究成果(如 Lintner,1965;Fama,1968),而且推动了资本 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理论的提出(如 Sharpe,1964;Mossin,1965)。 几乎与此同时(即 1950-1960 年代),公司财务领域奠基性的 MM 定理(Modigliani 和 Miller, 1958,1963)被提出。此后在 1970 年代,金融衍生品定价理论(如期权定价公式,Black 和 Scholes, 1973;Merton,1973)也问世了。以上提及的文献,是相关学说的提出者在 1980-2000 年代获得经济 学诺奖的重要基础。事实上,1981 至 2000 年的 20 年期间,经济学诺奖有 4 次颁给了现代微观金融 市场领域研究者。按人数计算,在此期间获奖的 25 人中,有 7 位来自上文提及的微观金融领域的学 者。由于这些诺奖得主的研究与金融实践紧密相关,他们的研究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的发展具有 极大的影响力,大大推动了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的发展,带动了泛金融行业快速膨胀,从而使得发 达市场国家(特别是美国)率先出现金融化现象。 12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三、微观企业金融化 经济金融化不仅包括泛金融行业的金融化,另外一个重要层面是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即非金 融企业金融投资占比和金融渠道获利占比日益提高。因为非金融企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构成,所以 这一领域的文献集中于实体经济金融化的研究。在这一分支的研究中,共识性的发现有三方面:一 是非金融企业的利润来源渠道日益倚重金融渠道,二是非金融微观企业的金融投资占比日益高涨, 三是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持有比率日益增长。 第一个方面,即非金融类微观企业的利润来源渠道日益倚重金融渠道,这是实体经济金融化研 究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微观企业通过金融渠道获取利润的方式逐渐占据主导,从这个角度考察实体 经济金融化问题,属于宏观问题的微观视角。Arrighi(1994)在其专著《货币与权力的游戏》中就 曾指出这一问题,之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受到社会学家或者社会经济学家的关注(例如 Krippner, 2005)。归纳起来,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微观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利润来源是否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渠 道而不是传统的商品生产与贸易渠道获得,来判断微观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程度。 有意思的是,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现象的关注,较早和较多地来自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专家。 例如,Krippner(2005)是观察并提出美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的代表性文献,作者是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文章对美国实体企业的利润来源渠道进行了细致的测算,根据 1950 至 2001 年的测算结果,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资占现金流收入在 1970 年之前一般不到 10%,此后一路上 涨,到 2001 年达到接近 50%的高位。 为了研究中国非金融企业利润积累渠道的变化,我们分析 2006-2016 年期间在中国 A 股上市的 非金融类企业的半年度财务数据,并计算这些企业从金融渠道中获得的利润占比情况(从金融渠道 获得的利润定义为企业的利息收入、分红收益以及资本利得的加总),结果汇报在图 3 中5。从图 3 中不难发现,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从金融渠道获利占比逐年升高,占比值在 10 年间从 3%的最低点 上升到接近 20%左右的最高点,尽管这个比重相较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然较低(根据 Krippner (2005)的计算,美国在 2000 年左右已经达到 40%),且该比率在 2007 年金融危机时期出现阶段性 下滑,但随着此后各种宽松政策的刺激又出现了较快增长,特别是 2010 年之后更是呈现明显持续上 扬的态势。2007-2008 年期间的非金融企业从金融渠道获利占比下滑,与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金融服务 业的经济利润占比不高的情况表现一致;而危机爆发以后不久,中国金融服务业的经济利润占比开 始回升,这与图 3 微观企业金融化的走势也比较一致。 5 根据 A 股上市非金融公司数据计算,剔除 ST 公司以及 2011 年之后上市企业数据,最终企业样本数量为 1902 个。 13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20 (%) 16 12 8 4 20 16 20 15 20 14 20 13 20 12 20 11 20 10 20 09 20 08 20 07 20 06 0 图 3 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A 股)从金融渠道获利占其当年净利润的比率 原始数据来源:WIND 资讯,经作者计算;金融渠道获利占比使用非金融企业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其他 综合收益等金融渠道获利加总除以营业利润。 最近的一项研究(张成思和张步昙,2016)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与实业投资率之 间的关系。该研究以非金融企业通过金融渠道获利占比日益上升作为金融化特征的切入点,对我国实业 投资率下降现象进行诠释,首先构建金融化环境下的微观企业投资决策模型,然后基于构建的理论模型 进行实证分析,检验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率的直接与间接影响。这一研究表明:中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 显著降低了实业投资率,并显著弱化了我国货币政策提振实体经济的效果;研究同时还表明,金融资产 风险收益错配也抑制了企业的实业投资,而且这种抑制效应随着微观企业金融化程度的提升而增强。 金融化对实体经济的负面效应似乎与其他研究彼此呼应,例如谢家智等人(2014)依据中国上市公 司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金融化将加剧“去工业化”和资产泡沫化产生的矛盾,不利于我国制造业的进 一步发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研究结论是基于全体上市公司混合数据的分析结果,如果考虑融资 约束条件和金融摩擦情形差异(例如 Li,2017)进行分层,金融化对不同类型的微观企业的实业投资影 响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进而也会影响到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影响效果的结论。因此,不宜轻易得出金 融化对实体经济发展必然具有破坏性的结论。 第二个方面,即非金融微观企业的金融投资占比日益高涨,也能反映实体经济金融化的程度。事实 上,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企业投资组合行为偏向金融投资的现象。 Krippner(2005)以及 Epstein 和 Jayadev(2005)的研究印证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业部门的金融资产配 置偏好,而 Demir(2009a)的实证研究以及 Bonizzi(2014)的综述研究都说明,新兴市场国家的实业部 14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门也出现了金融投资的偏好,特别是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这三个国家吸收的大量外部投资并未提升 固定资产的形成比例,却刺激了企业的金融投资偏好。 第三个方面,即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持有比例日益增长,反映了实体企业资产类别份额的变化, 尽管这一方面也能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实体企业对“金融”与“实业”的偏好,但资产类别份额的变化 (即金融资产持有比率)更偏向是一个静态指标,无法捕捉投资行为的变化情况,因此在理解实体经济 金融化方面与前两者相比略有局限。 根据已有研究(Froud 等,2000;Lazonick 和 O‟Sullivan,2000),微观企业以上三个方面的不同金融 化表现,都源自一个共同的经营理念的结构性转变,即本文之前所归纳的股东价值论的兴起。根据已有 的实证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不仅 OECD 国家的微观企业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更青睐金融投资而 减少固定资产投资(Stockhammer,2004;Crotty,2005;Dumenil 和 Levy,2005;Epstein 和 Jayadev, 2005),而且阿根廷、墨西哥和土耳其三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微观企业也存在类似的投资选择行为 (Demir,2009a,2009b)。 32 2 金融投资与实业投资回报率差(左轴) 金融渠道获利占比(右轴) 28 4 -6 0 20 16 -5 20 15 8 20 14 -4 20 13 12 20 12 -3 20 11 16 20 10 -2 20 09 20 20 08 -1 20 07 24 20 06 0 (%) (%) 1 图 4 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A 股)从金融渠道获利占其当年净利润的比率 原始数据来源:WIND 资讯,经作者计算;其中金融渠道获利占比使用非金融企业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其他综合收益等金融渠道获利加总除以营业利润;金融投资回报率是指金融渠道获利除以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包括货币资 金、持有至到期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以及应收股利和应收利息); 固定资产回报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资产减值损失)/经营资产(即运营资本+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等长期资产的净值)。 15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值得说明的是,股东价值论的兴起,固然是微观企业选择金融化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一因素的 背景是现代金融学宏微观范式结构性转变的典型反映(即以马科维茨 1952 年投资组合选择理论 (Markowitz,1952)的提出为代表,随后 CAPM、APT、MM 定理、期权定价模型和托宾 Q 等微观金融 学理论开始形成基本逻辑共识性的大发展,而传统宏观金融学理论(特别是利息理论、银行理论和货币 理论)却在 1950 年代之后分歧日渐加大而未能实现应有的基本逻辑的共识性快速发展),其对于微观 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是间接的6。更直接的影响因素可能是最近二三十年来各国先后出现的传统生产行业 利润率下降的普遍现象,而且金融业与生产行业利润率的缺口(即回报率差)以及企业的风险规避可能 是驱动企业从实业投资转向金融化的显著影响因素。哪个行业利润高(而且相对风险低),资本便涌向 哪个行业,甚至形成行业潮涌现象(林毅夫,2007;袁江和张成思,2009),这一现象是资本逐利天性 的本质体现。中国 2006-2016 年间的数据(图 4)似乎能够印证金融投资与实业投资回报率差驱动非金 融企业选择金融化的结果:图 4 显示,中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走势与金融行业的相对回报率走势高度 一致。这至少说明二者存在高度相关性(样本区间内相关系数计算结果为 0.889)。 从现实情况看,实体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本质上反映的是企业的投资组合选择(优化)问题。因此,要 想科学求证微观企业金融化的驱动机制,需要基于投资组合选择模型来刻画实体企业在金融资产和固定 资产投资上的选择行为。例如,我们可以构建一个二期或者多期优化模型来推演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可能 驱动因素,然后基于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理论建模过程中,可以假定代表性投资者(对应于实体 企业)投资的效用为标准的常系数绝对风险厌恶效用函数,然后进一步假设企业在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 这两类资产上的投资回报率服从正态分布,进而通过标准的优化条件获得微观企业金融化的解析表达式, 作为理论分析的基础。 根据以上设定,我们可以获得企业投资组合模型下的金融化驱动机制理论框架(表现为金融投资占 比受到金融与实业投资利差、实业投资风险占比等因素的影响),进而根据此理论框架对应的经济模型 转化为实证模型,并根据实证模型分析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对金融投资占比和金融渠道获利占比两个 指标分别进行考察)的驱动因素。基于 2006 年至 2016 年期间中国上市企业的数据进行估计,实证结果 表明,微观企业金融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金融投资与实业投资收益率缺口(金融投资占比和金融渠道获 利占比对应的回归系数分别在 1%和 5%的水平下显著),从而印证了资本逐利因素对微观企业金融化的 驱动效应。 6 宏观金融的微观基础发展、宏观环境变化以及体制机制的不同都导致宏观金融理论难以形成一致的逻辑结论;并且 宏观经济体的目标经常是多变的,所以没有微观经济主体明确和稳定。 16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四、商品金融化 随着经济发展和商贸的繁荣,资本逐利的天性也带来了商品金融化,不仅是大宗商品(commodity) 金融化和资产证券化,而且表现为普通商品(goods)金融化,即普通商品在交易过程中金融属性日益 增长。在商品金融化的已有文献中,Tang 和 Zhu(2017)所指的“商品金融化”重点在于讨论大宗商品 期货合约如何像典型金融资产(证券)一样运行,他们实际定义的是“金融化里的证券化”或者大宗期 货商品的金融化。而在中国,金融市场体系是以银行为主导的格局,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不是很高(特 别是金融产品的种类和金融法规的健全程度都比较欠缺)。因此,谁拥有资金,谁才有金融化的“资 本”。所以,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商品金融化其实是“证券化”或大宗商品期货合约问题。而在中国, 商品金融化的主要问题不是证券化,而是实物商品金融化。 遗憾的是,即使是中文文献,在讨论商品金融化问题时,也多是与西方文献类似,实际上讨论的都是 大宗商品期货问题,而非普通商品金融化问题。例如,崔明(2012)认为大宗商品金融化表现为经济系 统或金融市场削弱了商品的实际交易价值,使之变成可以用来交易的金融产品或金融衍生工具,期货市 场上机构投资者的增加带来对商品期货投资的增长,表现为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和剧烈波动。吕志平 (2013)认为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出现剧烈波动的主要成因是大宗商品被作为一种投资产品而成为全球投 资者的获利工具。孙国茂和陈国文(2013)提出,过多的货币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升高,商品期货市场交 易机制的完善促使衍生品市场和现货市场逐步金融化。罗嘉庆(2013)基于近代欧洲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的形成过程分析商品金融化对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促进作用,实质问题仍然是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问题。 李书彦(2014)发现大宗商品金融化包括交易主体金融化和价格形成金融化两个部分。大量机构投资者 和个人投机者都进入大宗商品的交易市场,参与期货交易的目的也从初始的套期保值逐渐转向套取价差 获利。田利辉和谭德凯(2014)通过分析美国股票指数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大宗商品现货价格波动, 指出期货市场具有金融传导功能,称此为大宗商品现货定价的金融化。 在西方视角里,大多数人理解金融化的逻辑是:原先用于消耗(短期内消费或长期内摊销)的商品 转变为具有价值储藏功能的资产,然后这种资产进一步被证券化,即在流动性和价格波动性上越来越趋 向于证券。而在中国的背景下,侧重点在于银行信用扩张与收缩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商品的金融化程度, 或称之为“金融化里的杠杆化”。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强调商品价格变动方式像不像证券,而且关注引 起这些价格变动的因素是不是由于该市场中信用供给状况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说,本文强调的是普通商品的交易机制中金融特性的逐渐渗透,从而带来普通商品价格决定 机制的微妙变化,真实的供给和需求状况只是部分决定因素,而金融资本的逐渐渗透使得普通商品的买 17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卖蒙上了厚厚的金融沙土,交易的过程更像商品所有权的转让,普通商品逐渐演化为一种类金融资产 (商品则成为该金融资产对应的标的),交易者购买的目的是为了转售所有权获利而并非使用商品本身。 因此,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定义的“商品金融化”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该商品的交易机制中 金融属性逐渐增强,以至于商品的价格决定越来越偏离实体层面的供给和需求因素,而越来越多地取决 于进入该市场资金量的大小,商品价格的波动性与金融产品的价格波动性更为接近。金融产品的价格经 常出现周期性大幅波动,而普通商品由于传统上是以消费为主要购买目的,只要商品市场供求平稳,一 般情况下价格不应该出现剧烈波动。金融资本进入商品市场后,由于金融资本的转移速度往往较快,因 此会推高商品价格的波动性。此外,商品不再单独作为商品在交易,而是将这种商品的所有权作为一种 金融资产(商品则成为该金融资产对应的标的)交易,交易者购买目的是为了转售所有权获利而非使用 商品本身。这层含义既不否认西方文献中所定义的大宗商品金融化是商品金融化的一种形式,又比 Tang 和 Xiong(2012)以及其他西方文献如(Tang 和 Zhu,2017)所定义的商品金融化外延更广,而且 侧重点有所不同。Tang 和 Xiong 等文中所指的“商品金融化”重点在于讨论期货合约如何像典型金融资 产(证券)一样运行,他们实际定义的是“金融化里的证券化”。 当然,仅从商品价格的波动性来看并不一定能准确衡量一种商品是否在经历金融化,例如成语中的 “洛阳纸贵”反映的是商品供需层面矛盾导致的价格变化。而投机行为本身也不一定是金融化,成语 “囤积居奇”体现了投机的思想,但只要这种价差仅是由于实体经济中供需失衡引起的,也不是金融化。 根据这种理解,伴随着期货交易的发展,大宗商品的金融化属性逐渐增强。最初,大宗商品的交易基本 都具有其真实交易背景,主要着眼于套期保值。然而,随着期货市场的发展,以投机为目的的交易逐渐 增多,大量期货交易的交易者并未持有底层商品合约。此时,交易的核心不再是商品标的本身,而是与 之对应的期货合约,因此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本质成为了金融交易,大宗商品步入了金融化的轨道,此 时进入该市场的资金规模出现大幅增加(Basak 和 Pavlova,2016),即资本密集程度大幅上升。 基于以上说明,为了不失一般性同时又突出中国商品金融化的特色,我们将商品价格波动性与商品 的资本密集度纳入评估商品金融化程度的指标体系。不过,如果仅从商品价格的波动性特征来看,可能 仅仅反映了市场经济下的价格行为。因此,我们强调商品金融化程度的多维度指标需要同时综合考虑, 而不能仅从单一指标进行测度和判断。本文最终将从五个维度对商品金融化进行测度。 商品金融化的第二层涵义指金融化是一个趋势相对稳定的演进过程,金融化商品的价格形成机制、 交易机制一旦形成,并不会由于价格的波动而导致过程中断,这个过程正常情况下是不可逆的,也因此 才能在语义上称之为“„„化”。有一些商品,短期内符合第一层次的定义,体现出了很强的金融属性, 但是过程是非常不稳定的,很容易退回到一般商品状态。例如,生姜大蒜的金融化非常不稳定,无法形 成被广泛接受的金融合约,一旦资金撤出,金融化过程就会中断,因此生姜大蒜的商品金融化程度属于 18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较低层次。而商品期货采用标准化合约,多边可接受性强,尽管价格可能有大起大落,但交易机制是规 范稳定的。因此,过程的稳定性可以纳入度量商品金融化程度高低的指标体系。直接整体量化金融化程 度的稳定性比较困难,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测度不同维度金融化属性的稳定性来判断整个金融化进程的稳 定性程度,时间序列分析中对于趋势项的估计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稳定性。指标的趋势项对于过去的指标 变化进行了平滑,因此捕捉了金融化进程中的稳定成分。如果趋势项也反映出了较强的金融化属性,则 可以认为金融化过程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仍考虑上面生姜大蒜的例子,尽管短时间内资本大量涌入,资 本密集度提高,但是随后由于资本轮动,资本密集度快速下降。这样的特征就会被归入波动项,不会直 接反映在趋势项中。 另外,金融化标的商品的流动性也是度量金融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从最严格的意义而言,一项 资产的流动性应当使用报价买卖价差(quote bid-ask spread)或者实际买卖价差(effective bid-ask spread)来 衡量,这一指标最直观的体现了资产因为流动性而损失的收益。但是,由于我们希望对各种商品的流动 性都能够进行判断,因此无法总是获得高频数据。现有文献中开发了许多使用低频数据度量流动性的方 法。这些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使用低频数据近似估计买卖价差,另一种是使用低频数据估计价 格效应(price impact)。在这其中,Amihud 比率(Amihud,2002)是最著名的流动性度量之一,且有许 多文献(如 Marshall et al., 2012,Johann 和 Theissen, 2017 等等)都指出了 Amihud 比率的优势。这一比率是 股票市场中衡量股票流动性最常用的方法,本质上度量了价格变化的流动性溢价补偿,其计算方式是使 用股票价格变化率(即收益率)与交易量比率的绝对值,结果用来度量流动性;其核心思想是同等规模 交易量带来的价格变化越大,则说明股票的流动性就越低;反之则说明股票流动性越高。与此类似,同 等规模交易带来的商品价格变化越大,则该商品的流动性就越差,金融化层次就越低。 Amihud 比率的原始文献采用了日度的交易数据,但是数据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于部分商品,日 度数据也是不可得的,可能只存在周度或者是月度的交易数据。不过,Amihud 比率是为了解决数据频 率不够而创造出的指标,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加总意义,因此这些指标的思想是可以用于更低频率的数据 的。仍以 Amihud 比率为例,如果现在只有月度数据,在一个月内的交易量引发的价格变化仍可在一定 程度上表征市场的流动性水平。因为如果某种商品的流动性不佳,市场规模很小,那么月度之内较小的 交易量仍会触发较大的价格变化。当然,就月度数据而言,由于商品的基本面可能会在这期间内变化, 因此需要控制一些额外的因素,可能需要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使用回归方法获得价格对于交易量的 敏感程度。 综合以上说明,要准确度量商品金融化的程度并不容易,因为商品金融化的定义存在模糊性,内涵和外 延并不是泾渭分明,单一维度指标必然难以完全表征商品金融化的特征。因此,商品金融化的度量指标 需要通过考虑金融产品交易过程的特征而使用多维度指标共同界定。综合以上对商品金融化的阐释和说 19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明,并结合商品金融化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张成思等,2014),本文提出商品金融化程度可以 从以下五方面进行考察: (1) 资本的密集度 每种商品市场都会存在一定的资本聚集度,大部分商品的资本聚集度,都受到实体层面供需因素的 调节,我们称这种资本密集度是正常的。但对于已经金融化的商品,这个市场里的资本密集度就不再受 供需因素的制约,而是可能出现任何形态,多数情况下是资本的“过密化”。所谓“过密化”,就是指 市场中的资本集聚程度远远超过了实现供给需求平衡时的常态水平。计算方法为: 资本的过密化程度 = (2) 市场中实际的资本集聚量 实现供需平衡时的正常资本量 − 1 × 100% 市场的杠杆率 杠杆率衡量一个经济主体用外部资源来为经济行为服务的能力。在中国以信贷作为最重要金融工具 的制度背景下,一种商品市场内流动的资金与交易参与主体自有资金和借贷资金的比例是衡量该商品市 场金融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杠杆率概念,可以看成是经济参与者个体杠杆率的加权平 均,从整体上看,便是该市场的杠杆率,计算方法为: 市场的杠杆率 = (3) 该市场流动资金总量 该市场流动资金量中自有资本数量 × 100% 商品的流动性 用市场上金融化标的商品的价格变化率与交易量比率的绝对值进行衡量,该指标越高,意味着商品 流动性越低,在这个维度上的金融化程度也对应越低;反之则流动性越高: Amihud 比率 = | 商品价格变化率 交易量 | × 100% 此外,作为稳健性检验,如果使用较为低频的数据,例如月度数据。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变化,可 以考虑使用时间序列模型,加入宏观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得到剔除其他因素后的商品价格对交易量的敏 感性。 (4) 价格的波动性 价格波动性指标沿袭了既有文献对大宗商品金融化度量的思路。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性高低可以比 较商品价格波动形态和证券产品的相近程度,如果相似程度较高,则金融化水平较高。理解商品价格的 波动性可以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研究它自身的波动性,例如使用波动性指数(Volatility Index);另一种 思路是假定典型的金融资产(如股票)是波动的,研究某商品的价格波动和该典型金融资产的波动有无 相关性,如果相关性高,则说明该商品从价格波动上来看和典型金融资产区别不大,这一指标在已有文 献中也被使用过。 (5) 过程的稳定性 20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商品金融化过程的稳定性通过测度上述 4 个指标的趋势项的水平值来度量。可以考虑通过 HP 滤波 法或者 Beveridge-Nelson 分解法将上述指标的时间序列分解为趋势项和短期波动项。如果趋势项也具有了 较高的金融化属性(如较高的资本密集度,较高的杠杆率,较好的流动性,较大的与金融资产的价格波 动的相关性),则可以认为金融化过程的稳定性已经较高。 一种商品开始金融化,可能是以上解释的五种指标都表现得非常突出,也有可能只表现为某个或者 部分特征,还有可能出现与以上五个指标的指向相反的情况。因此,要辨别一种商品的金融化程度高低, 我们建议综合考察以上五种指标。 在具体计算过程中,还需要确定不同指标的权重以及赋值方式。例如,如果没有特定偏好,五个指 标的权重可以相等;各指标赋值可以采取打分方法,当然此时还需要首先确定分档原则进而确定分值标 准。由于本文主题并非提供设计标准,因此具体设计过程不再赘述。 商品分类和金融化分层有对应关系,但又不是一一对应的。在图 5 中,我们对商品的分类有两种口 径,左边是按照实物用途属性分类,右边是按照货币金融属性分类。商品按照实物用途属性分类可以是 中间产品、消费品和资本品,其含义符合我们通常的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从货币 金融属性来看属于普通商品,供需决定价格,由于它们的保存期短和不具升值潜力,故不作为投资品。 但在特别的情况下,中间产品和消费品可能会成为投机品,靠短期投机操作赚取价差(图中用虚线示 意)。正常状态下,从用途上分类的资本品和从金融属性上分类的投资品是对应的。然而,资本品是很 容易在资金炒作的情况下变成投机品的。 普通商品向金融品转化需要经历金融化的过程。而投资品则可以天然地成为金融品或者类金融品, 例如债券、期货、股票、不动产产权等。由于投资品的种类、金融属性以及投资者的偏好不同,它们的 金融化程度可以分布在低、中、高三个不同层级。按照这个层级划分标准,普通商品的金融化一般停留 在中低层次,因为普通商品的存在周期短,给高层次金融化留下的空间小。单纯的投机品的金融化层次 最低,因为它缺乏过程的稳定性。当然,要对一种商品的金融化程度进行更精确的界定,需要针对前述 五个指标进行综合研判。 21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商品 中间商品 金融品 普通商品 消费品 投资品 资本品 投机品 低层级 金 融 化 中层级 高层级 图 5 商品向不同层级金融品的演化过程 事实上,根据图 5 演示的商品向金融品的演化过程,我们在图 6 中把经济中的交易标的分为金融产 品和商品两大类,金融产品包括债券和各种金融衍生品。我们还可以把商品类别划分为普通商品和资本 品(房地产就是典型的真实资本品);普通商品交易市场规模较小、没有规范交易机制、使用价值是其 主要属性。不过,资本品和普通商品在特定条件下(例如资本炒作),也可以向金融品或者类金融品转 化,在交易机制、市场规模、资本密集度和价格波动性等方面出现金融产品的典型特征。 金融品 交易标的 资本品 商品 普通商品 图 6 金融品和商品的分类(按交易标的)及转化 从本质上看,普通商品金融化的逻辑也是资本的逐利性。如果说微观企业的金融化是企业经营者在 生产端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结果,那么普通商品金融化就是投资人或者投机者在消 费端(商品市场)追求极致利润的结果。当然,普通商品金融化过程中,标的商品一般具有某种独特属 性,至少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稀缺性,或者可以形成垄断市场,标的商品价格在短期内出现大幅波动, 传统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发生扭曲。注意,投资或者投机是商品金融化的开端,商贸繁荣是商品金融化一 22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致的大背景,而泛金融业的金融化和微观企业金融化为商品金融化提供了不同层级金融化竞争和比较的 基础。与微观企业金融化的性质类似,商品金融化本身并不必然是破坏性的,商品金融化的理念甚至在 农村金融领域大有可为(陆磊,2013;高圣平,2014)。 五、多重逻辑的分歧与一致 金融的本质源自不同时期、不同个体之间资本调配的需要,在历史上多数时期均是服务业中的普通 成员。然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发展遭遇瓶颈期,同时受到“石油危 机”的冲击,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生产行业利润率大幅下滑,资本的逐利天性促使其进入诸多新兴产 业,或者对传统产业交易机制进行改造,与此相伴的是金融业在这 40 年间的迅猛发展,金融行业规模 迅速膨胀,利润占比逐年上升,对 GDP 贡献度和吸纳就业人数方面快速增长,部分学者将这一进程称 为经济金融化,而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泛金融业的金融化。泛金融化的形成逻辑与第三次科技革命、金 融监管放松以及金融自由化理念的兴起紧密相关,同时也与“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金融发展和金 融深化学说一脉相承;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泛金融业的金融化是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宏微观金融学 范式的转变所致。当然,泛金融行业的膨胀也带动了家庭部门的金融化,这方面的典型事实不仅发生在 西方发达国家,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日渐清晰。 与宏观领域泛金融业的金融化几乎并行出现的另外一个层次是实体企业(即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 我们称之为微观企业金融化。最近二十年来,西方学界大多关注的是泛金融业的金融化和微观企业的金 融化在发达国家的进展,而事实上中国在这两个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引人关注的局面。微观企业金融化 的形成,理论上源于股东价值论的兴起,是微观企业经营理念发生结构性转变的必然结果;在实践中, 微观企业金融化形成于泛金融业不断膨胀的大背景下,泛金融业的利润率超越生产行业利润率可能是驱 动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现实影响因素。从深层次看,金融业与实业在利润率格局上的这种变化,可能也反 映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展趋势(由工业、制造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因此并不能简单地把“金 融化”的性质定义为坏或是好,至少是一个中性的概念。 除了宏观和微观层面,金融化还有一个几乎被学界忽略却又颇具代表性的中观层次商品金融化。尽 管西方主流文献所指的商品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f commodities)是大宗商品金融化和资产证券化,但 是普通商品也出现了金融化现象(financialization of goods)。大宗商品金融化是在金融市场非常发达的背 景下形成的,而普通商品金融化是在金融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发生的,二者的形成逻辑并不相同,但是 本质上都是资本逐利的天性使然。虽然商品过度金融化会带来价格波动等负面冲击,但是商品金融化的 理念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如土地流转、农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山林资本转化等)具有正面启发意义。 23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本文对金融化以上三个层次进行逻辑阐释,提出大国金融化更具典型特征,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 大国金融化可以分为泛金融业金融化、微观企业金融化和普通商品金融化三个层次。从大国金融化的形 成逻辑来看,泛金融业的金融化既受到宏观金融发展理论的影响(特别是金融发展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 研究助推了大力发展金融行业的实践),又受到微观金融市场研究(特别是资产定价与公司金融)主导 下的微观金融实践带动,是理论和实践共同推动形成的格局;而微观金融市场研究也带动了股东价值论 的兴起,进而影响了微观企业的经营理念,再加之实践中企业趋利避险,从而驱动了微观企业金融化, 也是理论和实践共同推动的结果;对于普通商品金融化而言,最直接的形成逻辑是资本的逐利天性,而 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缺乏多元性可能是催生普通商品金融化的环境因素,因此普通商品金融化的格局主 要是实践推动的结果。 当然,本文使用“大国”的用意是暗示中国更贴近于本文论证的核心主体,特别是意在突出中国经 济总量大、市场规模大、资金(货币)总量大,但是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产品丰富程度低。因此,无论 从经济层面还是从金融层面来看,中国都是大国而非强国。从本质上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 金融化在宏微中观层次的逻辑根源都在于:经济体量大、市场规模大、资金总量大,国有大银行主导的 间接融资金融体系格局下金融产品的丰富程度不足。在此根源背景下,大国(相对于强国)宏观层次的 金融化更多体现的是规模发展而非竞争和效率提高;微观层次金融化也相应表现为企业投资于货币资产 (相较于股权资产)的比重更高;中观层次则表现为新兴的普通商品金融化特征,商品市场的特定部分 替代或者说补充了金融市场的部分职能。综合来看,三个层次的金融化都共同指向发展中大国对多元化 和市场化金融体系日益增长的需求。 尽管每个层次的金融化逻辑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差别和分歧,但是各个层次的金融化逻辑具有诸多 一致性。例如,各层次的金融化都说明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都反映出金融交易的极度 活跃性,本质上都是资本逐利天性的必然结果,因为三个层次的金融化都体现了资本向高利润行业(市 场)流动的本质:宏观层面泛金融业的膨胀反映了金融行业资本规模的膨胀,是资本向金融行业聚集的 结果,或者说金融行业本身就与资本是融为一体的;微观层面企业金融化行为的趋利避险也反映出资本 逐利因素对微观层次金融化的影响,这一点可以通过构建微观企业金融与实业两大类投资组合理论模型 得到验证;中观层面的商品金融化更直接地反映了资本逐利的特征,特别是中国的普通商品金融化表现 为哪个行业或者局部市场盈利高,资本便涌向哪个行业,形成行业潮涌现象(林毅夫,2007;袁江和张 成思,2009)。事实上,资本的逐利天性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贬义。在资本与真实产业(real sector) 良性互动的条件下,资本逐利就是一种资源有效配置的手段。所谓良性互动,关键是资本逐利背后有真 实产业背景(类似商业银行领域的真实票据论),涉及物资周转和产销过程,同时资本的行业集中度相 对合理。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从低利润向高利润率行业(市场)流动,而高利润率行业往往是生产更 24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有价值的产品或更缺乏资本的真实行业,此时逐利引发的资本流动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然,当资 本逐利与真实产业逐渐脱离甚至形成虚拟经济空转情况时,资本逐利导致经济脆弱性甚至带来金融危机 和经济危机的概率就会上升,此时资本逐利不再能发挥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 当然,大国金融化也更深层次地暗示出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出现了微妙的结构性变化(如中国三次产 业的结构调整)。这些微妙变化深刻地表明,金融化可以推动实体企业“产融”结合、提升企业市场活 跃度、甚至促进大国经济转型发展。相反,过度金融化则很可能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多重负面冲击,这些 负面冲击既包括增加经济体的脆弱性、延长危机时间、加剧资源错配,也包括加剧商品价格波动程度、 增加政府平抑价格波动的成本。美国 2008 年金融危机是典型案例之一,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发展实践中 也出现过一些典型的金融化过度带来的负面冲击案例。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都是金融化与真实经济的日 渐脱离形成虚拟经济空转现象。不过,负面冲击是随机冲击而不是系统性冲击,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其等 同于“矛盾的累积”甚至是“发展的陷阱”。随机冲击是否会引发危机,则需要具体评价其偏离均衡的 程度,一个基本判断标准就是金融化是否具有真实产业背景;当然,未来研究还可以着力设计更具体的 金融化均衡指标来进行测度(如张成思和张步昙(2015)提出的均衡杠杆率指标)。 展望未来,金融学界需要对各个层次金融化相关的典型事实和主流理论进一步深入探索和深刻反思, 如果能够找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平衡路径,甚至能够估算出不同层级金融化的均衡水平,则可以 帮助我们减少随机性,推进金融体系更好的运行。因此,金融化问题的研究不应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或社会学领域,而且要在金融学特别是货币金融学领域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给出构建完备 金融体系的可行性方案。如果有可能,相关研究还要提供更加细致的微观证据:例如,厘清金融化对不 同规模(如大型和中小型)和不同体制类型(如国企、民企)微观企业的主营业务的影响一致还是具有 异质性,这对国家是否需要制定差异性政策而言至关重要。只有做好这些基础性工作,才能真正实现 “好的金融”(有真实经济背景的金融)服务于国计民生的目标。 25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参考文献 崔明,2012:《大宗商品金融化的动因、争议与启示》,《现代管理科学》第 12 期,87-89。 高圣平,2014:《农地金融化的法律困境及出路》,《中国社会科学》第 8 期,148-208。 李书彦,2014:《大宗商品金融化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影响》,《农业经济问题》第 4 期,51-57。 林毅夫, 2007:《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建》,《经济研究》第 1 期,126-131。 罗嘉庆,2013:《商品金融化与产品定价机制变革》,《产经评论》第 3 期,141-148。 陆磊,2013:《开启伟大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中国农村金融》第 3 期,1-2。 吕志平,2013:《大宗商品金融化问题研究》,《湖北社会科学》第 2 期,77-80。 孙国茂,陈国文,2013:《商品金融化形成机理研究》,《济南大学学报》第 6 期,1-9。 田利辉,谭德凯,2014:《大宗商品现货定价的金融化和美国化问题》,《中国工业经济》第 10 期, 72-84。 谢家智,王文涛,江源,2014:《制造业金融化、政府控制与技术创新》,《经济学动态》第 11 期, 78-88。 袁江,张成思,2009:《强制性技术变迁、不平衡增长与中国经济周期模型》,《经济研究》第 12 期, 17-29。 张成思,刘泽豪,罗煜,2014:《中国商品金融化分层与通货膨胀驱动机制》,《经济研究》第 1 期, 140-154。 张成思,张步昙,2015,《再论金融与实体经济:经济金融化视角》,《经济学动态》第 6 期,56-66。 张成思,张步昙,2016:《中国实业投资率下降之谜:经济金融化视角》,《经济研究》第 12 期,3246。 Amihud, Y. (2002), “Illiquidity and Stock Returns: Cross-Section and Time-Series Effects”, 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 5(1), 31-56. Amin, S. (1996),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3(2), 216-59. Amin, S. (2003), Obsolescent Capit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Arrighi, G. (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Arrighi, G. (2003),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turbulence”, New Left Review, 20(2), 5-71. Basak, S., and A. Pavlova (2016), “A model of financialization of Commodities”, Journal of Finance, 71(4), 1511-1556. Black, F., and M. Scholes (1973), “The pricing of options and corporate liabil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3), 637-654. 26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Bonizzi, B. (2014), “Financ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2(4), 83-107. Chen, Z., R. Ibbotson, and W.Y. Hu (2013), “Liquidity as an investment style”,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69(3), 30-44. Cochrane, J. H. (2013), “Finance: Function Matters, Not Siz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2), 29-50. Crotty, J. (1990), “Owner-manager conflict and financial theory of investment stability: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Keynes, Tobin, and Minsky”,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12(4), 519-42. Crotty, J. (2005), “The neoliberal paradox: the impact of destructive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modern‟ financial markets on nonfinancial corpor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neoliberal era”,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77-110. Davis, G.F., and S. Kim (2015),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1), 203-221. Demir, F. (2009a),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private investment and portfolio choice: financialization of real sectors in emerging marke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8(2), 314-324. Demir, F. (2009b), “Capital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financialization of real sectors in emerging markets: private investment and cash flow relationship”, World Development, 37(5), 953-964. Dumenil, G., and D. Levy (2005), “Costs and benefits of neoliberalism: a class analysis”,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7-45. Epstein, G. (2005),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Epstein, G., and A. Jayadev (2005), “The rise of rentier incomes in OECD countries: financialization, central bank policy and labor solidarity”, Financialization and World Economy,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46-74. Erb, C.B., and C. R. Harvey (2006), “The strategic and tactical value of commodity futures”,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62(2), 69-97. Fama, E. F. (1968), “Risk, return and equilibrium: some clarifying comments”, Journal of Finance, 23(1), 29-40. Foster, J. (2007),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58(11), 1-14. Froud, J., Haslam, C., Johal, S., and K. Williams (2000), “Shareholder value and financialization: consultancy promises, management moves”, Economy and Society, 29(1), 80-120. Froud, J., Johal, S., and K. Williams (2002),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coupon pool”, Capital and Class, 26(3), 119-151. Goldsmith, R.W. (1969),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Gorton, G., and K. Rouwenhorst (2006), “Facts and fantasies about commodity futures”,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62(2), 47-68. Greenwood, R., and D.Scharfstein (2013), “The growth of fin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2), 3-28. 27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Gurley J.G., and E. S. Shaw (1955), “Financial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4), 515-538.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ilferding, R. (1910), Finance Capital: A Study in the Latest Phas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King, R. G., and R. Levine (1993),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3), 681-737. Kirilenko, A. A., and A. W. Lo (2013) “Moore‟s Law versus Murphy‟s Law: Algorithmic Trading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2), 51-72. Kliman, A., and S. Williams (2015), “Why „financialization‟ hasn‟t depressed U.S. productive investment”,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9(1), 67-92. Krippner, G. (2005),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Socio-Economic Review, 3(2), 173-208. Lapavitsas, C. (2013),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m: profiting without producing?”, City, 17(6), 792-805. Lazonick, W., and M. O'sullivan (2000), “Maximizing shareholder value: a new ideology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Economy and Society, 29(1), 13-35. Li, D. (2017), “Uncertainty, financial frictions and investment sensitivity to cash flow”,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Lintner, J. (1965), “The valuation of risk assets and the selection of risky investments in stock portfolios and capital budge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7(1), 13-37. Malkiel, B. G. (2013), “Asset Management Fees and the Growth of Financ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2), 97-108. Markowitz, H.M. (1952), “Portfolio Selection”, The Journal of Finance, 7(1), 77-91. Marshall, B. R., N. H. Nguyen and N. Visaltanachoti (2012), “Commodity liquidity measurement and transaction cost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5(2), 599–638. Johann, T., and E. Theissen (2017), “The best in tow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ow-frequency liquidity estimators”,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905032. McKinnon, R.I. (1973),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Merton, R. C. (1973), “Theory of rational option pricing”,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4(1), 141-183. Miller, M. H. (2000), “The history of finance: an eyewitness account”,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13(2), 8-14. 28 货币金融评论 2020 年第 07-08 期 Modigliani, F., and M. Miller (1958),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3), 261-297. Modigliani, F., and M. Miller (1963), “Corporate income taxes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a corre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3), 433-443. Mossin, Jan. (1966), “Equilibrium in a capital asset market”, Econometrica, 34(4), 768-783. Orhangazi, O. (2008),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US Economy,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Patrick H. (1966), “Financial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elopment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4(2), 174-189. Philippon, T., and A.Reshef (2013), “An International Look at the Growth of Modern Fin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2), 73-96. Rajan, R. G., and L. Zingales(1998),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3), 559-586. Rajan, R. G., and L. Zingales(2003), “The great reversals: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9(1), 5-50. Rousseau, P., and P. Wachtel (2011), “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epening on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Inquiry, 49(1), 276-288. Schumpeter, J. A. (1911),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harpe, W. F. (1964), “Capital asset prices: 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 Journal of Finance, 19(3), 425-442. Shaw, E.S. (1973),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Stockhammer, E. (2004),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slowdown of accumula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8(5), 719-741. Stockhammer, E., and L. Grafl (2010), “Financial uncertainty and business investment”,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2(4), 551-568. Tang, K., and W.Xiong (2012), “Index Investment 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Commodities,”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68(6), 2012, 54-74. Tang, K., and H. Zhu (2017), “Commodities as collateral”, Forthcoming,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an Treeck, T.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debate on „financialization‟ - a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6(5), 907-944.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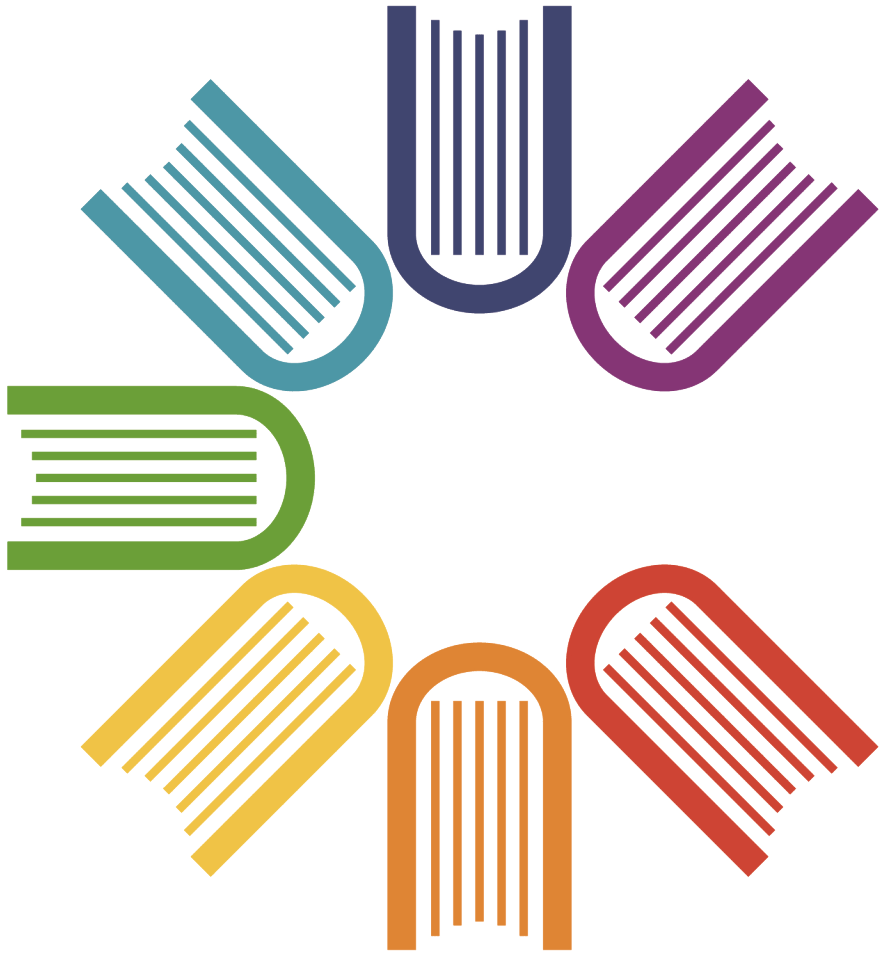
 《货币金融评论》2020年第7-8期.pdf
《货币金融评论》2020年第7-8期.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