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强意识形态、弱意识形态与理性共识.pdf
2011 年第 4 期 强意识形态、弱意识形态与理性共识 * —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看意识形态斗争策略 —— 王晓升 [摘 要 ] 哈贝马斯所构想的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是要通过理性商谈来达成理性共识 , 这种 理性共识实际上是弱意识形态。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 “再封建化” 了, 人们在公共领域中展开了公 开的利益斗争, 这种斗争表现为强意识形态。 在公共领域中, 只要采取一定的程序而使所有的人平等参与商 谈, 那么理性共识是可能的。 然而在公共领域中, 大众和公众又是混合在一起的, 意识形态斗争在策略上就 是利用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 关键词 ] 意识形态 弱意识形态 强意识形态 理性共识 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11 ) 04-0014-08 在社会生活中, 人们总是会就政治法律问题、 文学艺术问题、 伦理道德问题等展开讨论。 这种讨论 在不同程度上会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 但是, 这种讨论是不是可以得到理性共识呢? 如果可以, 那么理 性共识和意识形态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 在意识形态的 斗争中, 人们又是如何利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呢? 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虽然不是主要研究这个问题的, 但是它却给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启示。 一、 弱意识形态: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 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 17 、 18 世纪以来欧洲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个重要的 变化, 这就是在私人领 —政治公共领域 (在这里, 我们主要讨论政治公共领域, 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之间出现了一个公共领域—— 而不考虑文学公共领域)。 这个公共领域是在反对封建的统治权威的基础上产生的。 参与公共领域的人 是私人, 他们不是要瓜分权力, 而是要改变权力的基础, 即在公共领域中对权力进行监督。 参与经济活 动的私人就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自由讨论, 从而保护他们的私人利益。 哈贝马斯把这样理解的公共 领域称为 “公共领域的自由主义模式”。 按照这样的自由主义模式 : “它保证社会是一个私人自主的领 域, 并将公共权力限于有限功能之上; 在这两个领域之间, 存在着一个私人的领域, 他们集聚而成为公 众; 作为国家的公民, 他们调节国家和市民社会的需要; 其理想目标是在这种公共领域的调节下, 将政 治权力转化为 ‘理性的’ 权力。” [1] (P129) (译文略改)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改革开放视阈下我国社会意识变动趋向与规律研究” (10zd&048 )、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 (08AZX001 )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晓升,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湖北 武汉, 430074 )。 - 14 - 按照他的看法, 最初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向人们自由开放的, 人们可以自主参与其中。 他强调,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成败始终都离不开普遍开放的原则。” [2] (P94) 对于他来说, 开放性原则是保证公共领 域的公共性的首要条件。 他并不否认参与其中的个人都是利益主体, 都是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 但是他 强调, 参与公共领域的人不仅仅是作为私人, 而且还作为 “公众” 一员参与其中的活动。 作为公众一 员, 一个人就要摆脱自己的私人利益, 而以一个具有人性的人的身份来参与公共领域 。 哈贝马斯强调, 在私人领域中, 资产阶级的个人既是财产的所有者, 又是众人中的一员, 而在公共领域中也是如此。 他 说 , “成熟的资产阶 级公共领域永远 都 是建立在组成 公众的私人所具 有 的双重角色 , 即作为物 主 (私 人—— —引者注) 和人 (普遍的人—— —引者注) 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 [2] (P59)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 虽然 参与公共领域中的人都是私人, 但是公共领域中的私人是聚集为公众的私人。 作为公众, 这些私人是以 人的身份来参与公共活动的。 他们参与公共讨论的目的是要就他们的 “主体性的经验达成共识”。 [2] (P59) 哈贝马斯认为,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种报纸和刊物的出现。 一方面, 言 论自由在法律上得到保证, 另一方面, 政治权力机关行为, 包括政府事务和议会的程序都被要求向公众 开放。 公共领域对于政治权力领域的监督因此获得了永久的合法性 。 公共舆论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诞生的初期, 一些报纸为了生存, 必须不断地表现自己, 它们要不断地为争取舆论 的自由空间, 为争取公共性原则而进行斗争。 那个时候的报纸虽然也要借助于商业化的运作, 需要有一 个 “可靠的商业基础, 但并没有使报刊业本身商业化”。 [2] (P220) 它主要还是用来传递信息, 为人们进行公 共讨论提供一个平台。 因此, 这个时候, “它首先关注的是确立公众的批评功能; 因此在投入经营企业 的资本时, 如果考虑到回报的话, 也仅仅是第二位的。” [2] (P221)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 资产阶级的政治公共 领域主要还是用来批评政府的。 批判功能在这里居于首要地位, 由此 “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报刊业才能 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力”。 [2] (P221) 然而问题在于, 具有意识形态批评特点的报纸业为什么又能够摆脱意识形 态的压力呢? 在哈贝马斯看来,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 这是因为, 参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都 是私人。 在这里, “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 ‘个人’ 和 ‘公民’ 之间没有差别。” [2] (P94) 他们每个人既是私 有者, 同时又作为公民来保护财产秩序, 保护私有财产 。 显然公共领域中的私人是有自己的利益考虑 的, 但是他们却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 。 哈贝马斯指出, 意识形态的根源就在于 , “‘财产所有 者’ 和 ‘人本身’ 混同起来。 这种混同不仅发生在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那种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中 的私人所扮演的公众的角色中—— —其中政治公共领域与文学公共领域也被混同起来了, 而且也发生在公 共舆论中, 在其中, 阶级利益通 过 公 开 论 辩 的 中 介 而 具 有 普 遍 性 的 假 象 — —— 也 就 是 统 治 与 统 治 在 纯 粹 理 性 中 的 消 解 被 混 同 起 来 了 。 ” [ 2] ( P97 ) ( 译 文 有 较 大 改 动 , 参 见 J ürgen Habermas , Strukturwandel der 魻ffentlichkeit , SuhrkampFrankfurt am Main , 1990, S. 111. ) 从这里可以看 出 , 资产阶级公 共领域从 一开始就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的特点。 这种意识形态的特点表现在, 私人扮演成公众, 阶级利益取得了共 同利益的形式, 而资产阶级的统治似乎纯粹是理性的统治。 显然, 哈贝马斯并不否认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的意识形态特征。 而哈贝马斯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含义和马克思当年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所说的意识形 态是一致的。 但是, 哈贝马斯认为, 这种意识形态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力。 这是因为, “在当时, 阶 级利益必然在客观上与普遍利益重合, 至少阶级观念会被认为是公共舆论, 其中介是公众的批判, 结果 则是合理性。” [2] (P96) 在他看来,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当时是具有合理性的, 而不是什么赤裸裸地为资 产阶级利益辩护的。 为此, 他还强调, “只是随着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建立, 知识分子报刊才从意识形 态观点的压力下解放出来, 从事理性的公共运用。” [1] (P130) 实际上, 意识形态工作的本质就是要使特殊利 益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 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恰恰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把这种意识形态称为弱意 识形态。 按照哈贝马斯的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的模式, 所有的相关人都是作为平等的参与者而参与商谈的 , - 15 - 他们仅仅用理由来说服人。 而在这种商谈中, 人们所得到的共同结论就具有了理性共识的特征。 或者可 以说, 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公共领域在这里被去意识形态化了。 然而, 这种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的理想 却从来没有实现过。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的全面潜能从来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实 现。” [3] (P59) 这是为什么呢? 哈贝马斯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模式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 在公共领域的商谈中, 人们都要提供理 由, 用理由来说服其他人。 但是, 人们提出的理由有很多, 有些理由会作为理由而被接受, 而有些理由 则不被作为理由。 或者说, 公共领域中的人们会拒绝接受某些理由。 哈贝马斯强调: “决定性的理由必 须在原则上能够为所有分享 ‘我们的’ 传统和强有力价值态度的成员所接受。” [4] (P133) 然而问题恰恰就出 现在 “我们的” 传统和强有力的价值态度上。 这是因为, 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某些占主导地位的价值 观。 在这些主导价值观的基础上, 某些理由会被作为理由而接受, 而某些理由会受到排斥, 被认为是错 误的。 一些学者指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 “主要为男性所保留的, 哈贝马斯虽然意识到, 资产阶级公 共领域中妇女的边缘化, 意识到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家长制特点, 但是我们似乎可以说, 在他写作 《公共 领域的结构转型》 的时候, 他并没有估计到这个问题的全部意义。” [5] (P181) 于是, 在这里妇女平等权利的 价值观就处于边缘地位。 在哈贝马斯所说的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中, 必定会存在着这样一些非主导 的价值观。 哈贝马斯虽然看到了社会中存在着一些非主导的意识形态 , 但是他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处于边缘地位的价值观在这里, 无法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进行平等的商谈。 边缘人物的思想必然会受 到排斥。 从这个意义上说, 哈贝马斯所说的理性共识, 实际上就是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而 哈贝马斯所信奉的就是这种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一种具有理性共识形式的意识形态: 所有人的 个人自主权利得到保障。 新兴的资产阶级都需要保障个人自由权利来对付封建统治。 为了保障个人自由 权利, 而反对封建的等级统治, 他们在原则上会不管个人差别而平等地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 二、 强意识形态: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 然而, 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后, 私人领域中的不平等越来越突出。 这种不平等也渗透到了公共领 域。 一些人要借助于公共领域来证明自己的利益的正当性, 而另一些人则要借助于公共领域来争取自己 的平等利益。 自由资本主义的理想的公共领域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破坏。 哈贝马斯把这种自由主 义模式在公共领域的衰退称为 “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 在哈贝马斯看来, 这种 “再封建化” 表现在两 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私人利益进入公共领域。 随着公共领域的传播效率和范围的提高, 公共领域也获得 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许多私营机构通过广告竞争而不是价格竞争来获得自己的利益 。 哈贝马斯指出, “由于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被用来做商业广告, 作为私有财产所有者的私人也就作为公众的私人产生 了直接的影响。” [2] (P225) 另一方面,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私人机构不仅会通过广告等来获取利益, 而且 还使这种广告具有政治性质。 它们会采取一些宣传技术, 来进行 “舆论管理”。 这种舆论管理被称为公 关实践。 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 “正当各种商品拥有者之间的横向竞争通过广告侵入了公共领域之时 , 资本主义的这种竞争基础也被拖入了政党冲突; 而且阶级利益之间的纵向竞争也已经进入了公共领域。” [2] (P228) 与此同时, 它们还会采取许多公关策略, 比如它们可以制造新闻, 从而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此外, 在现代社会, 新的传媒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 “所产生的新闻威力也相当惊人, 因此, 在有些国家里这 些媒体从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管理或控制。” [2] (P223) 在哈贝马斯看来,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报刊业和新 媒体发展有一个新特点, 就是那些由公众组成的私人机构演变成为 “官方机构”。 他说, “在英国、 法国 和德国, 这些新媒体是官方和半官方的组织, 因为如果不这样, 他们的传播功能就不可能得到充分保 护, 从而避免受到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功能的侵犯。” [2] (P224) 在哈贝马斯看来, 当政治权力和私人利益入侵到公共领域的时候, 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也发生变化 了。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公共领域丧失了沟通的功能。 公众不再能够像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样参与公共 领域的自由讨论。 他说: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公共领域变成了一座宫廷, 公众可以瞻仰其所展示出 - 16 - 来的声望, 但不能对它自身提出批判。” [2] (P225) 这就是说,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公众已经被排除在公共 领域之外了, 公共领域失去了其公共性。 虽然公共领域失去了其公共性, 但是, 各种利益集团会进行政 治上的操作而把公共性 “制造” 出来。 各种宣传活动就是 “制造” 公共性的活动。 哈贝马斯说, “‘宣传 工作’ 一词即已表明, 公共性过去是代表者表明立场所确定的, 并且通过永恒的传统象征符号而一直得 到保障, 而今, 公共性必须依靠精心策划和具体事例来人为地加以制造。 今天, 认同的动力只能有待于 —公共性必须加以 ‘制造’, 它已不再 ‘存在’。” [2](P236) 按照这样的分析,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创造—— 公共领域不再为人们之间的自由交流提供平台, 而是各种社会集团和利益的竞技场。 各个利益集团通过 宣传而努力表明自己能够代表公共利益。 这种制造出来的公共性赋予这些利益集团以各种 “光环” 和 “声望”。 而这种光环和声望原来是被赋予那些宫廷贵族的, 而现在被赋予了各种利益集团。 这意味着,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公共领域具有了代表性公共领域的特点, 它被 “封建化” 了。 这种 “再封建化” 了的公共领域给公众所提供的不是具有理性共识形式的意识形态, 而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 —一种为特 定的利益辩护的意识形态。 理性共识形式的意识形态是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意识形态, 而赤裸裸 的强意识形态则是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妥协, 并把这种妥协的结果说成是对大众有利的。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 人们之间的利益斗争发生在私人领域或者市场竞争的领域, 而不会在公共领 域发生。 这是因为, 在公共领域, 所有的参与者是以人的身份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的。 于是, 在早期资 本主义时代, 个人之间的差别不表现在公共领域。 虽然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存在着一些边缘团体, 但是这 些边缘团体在某种程度上最初都够接受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共同理想, 或者说, 接受资产阶级的平 等、 自由的意识形态理想。 然而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起来, 不同团体之间的差别, 不同的利益斗争就 出现了。 如果说早期资产阶级在公共领域所进行的反封建的斗争中所凸显的是 “人” 的角色的话, 那么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 参与公共领域的都是 “物主”, 是财产所有者。 这些财产的所有者是不平等的。 他 们必然会在公共领域进行利益斗争。 这种利益斗争就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新特点。 在这个 时候, 不同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 任何一个阶级都不能把自己的利益简单地说成是代表了 公共利益。 马克思最早发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这种意识形态斗争的新特点 。 哈贝马斯说: “马克思的批评摧毁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依靠的一切虚构。” [2](P142) 这是因为, 马克思认为, “所有者” 和 “人” 是不同的。 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中的问题就是把 “所有者” 和 “人” 等同起来了。 [2] (P142) 这就是 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关于抽象人的观念。 于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 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就表现在 “过去被推入私人领域的冲突现在进入了公共领域。” [1] (P131) 哈贝马斯认为,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以理性共识形式出现的意识形态不再可能。 按照早期资产 阶级的 “理性共识” —一种弱化的意识形态, —— 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基础, 市场中竞争完全是个人的 自由竞争。 社会的正义安排就体现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中。 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阶段, 私人领 域和政治权力领域开始干预公共领域, 并在公共领域展开公开的利益斗争。 由此普兰·强生指出, “一旦 阶级分裂社会的结构特性凸显出来, 公共领域就不能再认为, 其中的所有的参与者都有能力通过他们自 己的私人活动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公正内在于交易中’ 的观念的意识形态特性被揭示出来了, 这意味 着, 私人自主并不是可以普遍获得的, 而是依赖于特定的人的成就和财富。” [6] (P223) 哈贝马斯所期待的是 重新恢复这种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 而这种权威地位就是要使这种意识形态具有理性共 识的形式。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不再是理性共识的面具下的意识形态 , 而是不同利 益之间斗争的表 现。 公共领域所达到的就是这种利益的妥协。 哈贝马斯指出, 公共领域 “成为一个利益竞争的场所, 这 些利益竞争常以暴力对抗的形式出现。 法律几乎不能理解为产生于进行公共讨论的私人的共识, 而明显 是从 ‘街道的压力’ 之下产生的。 他们或多或少地以不加伪装的形式在私人利益之间达成妥协 。” [1] (P131) 在这里, “批判讨论中所达成的共识让位于非公共的妥协或者直接贯彻的妥协。” [2](P204) 为了达成这种妥 - 17 - 协, 南希·弗雷泽强调, 现代社会民主 制度应该照顾到那些被忽视的社会群体、 重视边缘化的文化等, 使所有的群体、 文化都能够 “均衡参与” (participatory parity )。 她说: “均衡参与的理想最好通过多样的 公众, 而不是单一的公众来实现。 这无论对于分层社会来说, 还是对于平均主义的、 多元文化的社会来 说, 也就是说, 对于各种不同的理由来说, 都是正确的。” [3] (P70) 弗雷泽的这个方案不过是对哈贝马斯的 程序主义的商谈民主理论的一个补充。 她和哈贝马斯一样, 要重新恢复自由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 这也 表现了他们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念。 从哈贝马斯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哈贝马斯看来, 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特征所发生的 变化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的影响。 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表现为, 行政领域和经济领域对于 公共领域的入侵。 这就是说, 哈贝马斯是从社会结构的政治经济分析中来理解意识形态特征的变化的 。 这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观。 但是其他一些学者也指出, 公共领域内部存在着诸多内 部差异和斗争。 [7] (P358) 所有这些因素都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迫使公共领域在一定程度上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 领域和私人领域。 因此, 对公共领域的政治经济分析, 不能导致极端的经济还原论。 [7] (P359) 而哈贝马斯在 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斗争策略的研究上, 恰恰就表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还原论的特点。 三、 理性共识: 公共领域中的程序性商谈 如果说早期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形成使一种弱意识形态成为可能, 而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入侵导 致了强意识形态的出现, 那么理性共识究竟是不是可能呢? 如果可能的话, 究竟在哪些问题上, 我们可 以达成理性共识呢? 哈贝马斯在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一书中对于公共领域中立性的理解, 对于程序正 义的商议民主模式的建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认为, 公共领域中的商谈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中立的。 他认为, 如果公共领域中的商谈是按照一 定的程序而进行的中立的商谈, 那么这就是一种理性的商谈。 而这种理性的商谈就可以从意识形态的压 力下解放出来。 那么为什么一定的商谈程序能够有中立性呢? 哈贝马斯提出了三个方面的理由 。 第一个理由是, 如 果公共领域中的讨论把正义看作是高于善的 话, 那么这个讨论就是中立的。 他说: “中立性的含义首先在于论辩逻辑所论证的正义对于善的优先性, 也就是关于良好生活的问题退居于关于正义问题之后。” [4] (P383) 这就是说, 在公共领域的商谈中, 许多人 都会有自己的利益。 不同的人们对于美好生活有各自不同的理解, 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 在这里, 人们 必然会发生利益冲突。 为了解决这里的冲突, 这种商谈就应该进一步上升到 “正义商谈”。 在这种商谈 中, 人们要考察 “在承认这些分歧的同时, 什么是平等地有利于所有参与者的。” [4](P385) 第二个理由是, 公共领域中的商谈必然涉及到个人生活领域中的问题。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 公共领域中所讨论的课题虽 然是从生活领域中产生的。 但是究竟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在公共领域中讨论, 什么样的问题纯粹属于私人 问题? 这就需要在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加以解决。 只有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才成为公共领域中人们 共同关注的问题。 公共领域的这种筛选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私人利益对公共领域的干扰。 [4] (P388) 第三 个理由是, 虽然不同的人可以在公共领域中发挥其影响力, 但这种影响力是在公众的普遍赞同中获得 的。 哈贝马斯指出, “活动者通过公共交往所获得的政治影响, 归根结底必须建立在一个结构平等的非 专业人员公众集体的共鸣, 甚至同意基础之上。” [4] (P450) 虽然某些人或者某个团体在公共领域中发挥作用, 但这种作用也必须建立在参与人员的平等商谈以及所有相关人的理性赞同的基础上。 而这种赞同是不能 通过金钱的收买或者权力的威胁而获得的。 他说: “那种仅仅由于暗中注入金钱或组织权力才能造成的 公共意见, 一旦这种社会权力来源昭示于众, 其可信性立刻就化为乌有。 公共意见可以操纵, 但不可以 公开收买, 也不可以公开勒索。” [4] (P451) 在他看来,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政治权力领域、 私人领域侵入了公共领域, 人们无法进行平等 的商谈。 如果我们通过一定的程序来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商谈过程, 那么在这个时候, 人们 在商谈过程中就只能通过理由来说服人。 而借助于这种自由商谈而达到的结果就是一种理性共识。 这种 - 18 - 理性共识与意识形态是不同的。 这是因为, 与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不同, 在这里所有的相关人士都可以 作为平等的商谈参与者而就有关问题展开讨论 。 对于这种讨论的结果, 人们没有预设任何理想的目标。 或者说, 对于究竟怎样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 人们不存在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 对他们来说, 只要按 照程序进行商谈, 其所得到的结果就是正义的。 他们没有独立于程序之外的正义标准。 如果有了独立于 程序的正义标准, 那么这种商谈所达到的虽然也是理性共识, 但是, 这种共识就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 这是因为, 正义标准是在一定的价值标准下被设定的。 而在后期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的商谈模式中, 是 不存在一个独立于程序的正义标准的。 相反, 在早期的公共领域中, 市场领域的自由竞争潜在地成为正 义的标准。 这个正义标准是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征的。 如果说, 在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中, 哈 贝马斯也承认, 参与公共领域商谈的人们可以达成理性的共识的话, 那么在他看来, 那种理性共识是贯 彻了自由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理性共识。 而现在这种理性共识则不同了, 这是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理性共 识。 在这里, 我们通过他对于三个不同层次上的商谈的特征分析来说明强意识形态、 弱意识形态和理性 共识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层次的商谈是妥协的谈判。 在这里不同的利益之间展开谈判。 只要人们有合作的诚意, 只要 各方都有自己的代表, 都按照程序来进行的, 那么这种妥协的谈判是正义的。 这种正义的谈判是纯粹的 利益斗争。 这种谈判具有赤裸裸的意识形态的特点。 第二个层次的商谈是政治伦理的商谈。 这种商谈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 这种商谈是指一定的民族国家范围内, 政治共同体的人们就他们的共同生活目标所进行的商谈。 人们在 这种商谈中要达到共识。 这种共识既不同于妥协, 也不同于人们在事实问题或者正义问题上所达成的一 致认识。 [4] (P221) 这就是说, 在一定的民族国家中, 人们进行的商谈要受到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的影响, 同 时又要在这种影响下, 讨论什么是他们共同期待的美好生活。 于是人们在商谈中, 妥协的因素以及正义 的因素都在其中发挥作用。 这就是说, 在民族国家就宪法制定等问题进行的讨论中 , 人们既要进行妥 协, 又要进行公正的商谈。 第三个层次的商谈是道德的商谈。 这种道德的商谈只承认理由的力量, 而任何其他的力量都不发挥 作用。 这里的商谈涉及到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在这里, 人们得到的是完全正义的结果。 哈贝马斯 也把这种商谈称为正义的商谈。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正义的商谈所达到的结果具有类似于真理的性质。 从哈贝马斯对于三种商谈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种妥协的商谈, 是要承认不同的人们之间 的利益差异, 社会力量的差异, 并在这种差异的基础上达成妥协。 这种妥协的结果是强意识形态斗争的 表现, 是强势社会力量的意志的体现。 而第二种商谈, 既有妥协的成分, 也有正义的要素。 这种商谈的 结果是以理性共识形式出现的意识形态。 比如, 一个民族国家的人们对于他们的美好生活的共同期待 , 这种期待在政治制度中表现出来。 这种政治制度也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 但这是弱意识形态。 对于哈贝 马斯来说, 只有最后一种商谈, 也就是正义的商谈是完全按照自由商谈的模式进行的。 这种商谈的结果 类似于真理, 是完全的理性共识。 这样, 哈贝马斯就改变了他早期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领域的认识, 不再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大 众的结合体。 他承认, 虽然在公共领域中, 人们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斗争, 即不同社会团体为自己利益 的合法性而斗争, 但是, 在福利国家中, 只要程序主义的法治国家观念得到贯彻, 那么在公共领域中, 人们还是能够得到理性共识的。 四、 大众性与公共性: 意识形态斗争策略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利益的斗争从私人领域进入了公共领域。 于是公共领域中的社会团体从公众 转变成为大众。 在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分析中, 哈贝马斯还在一定程度上把公众 (das Publikum ) 和大 众 (die Masse) 区分开来。 在这里, 大众主要是指追求自己利益的团体, 而公众是讨论公共问题的私人 汇聚。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 虽然大众和公众都有私人利益, 但是他们处理私人利益的方式是不同的。 大 - 19 - 众是具有类似私人利益的人群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参与公共领域 , 他们是为了私人利益而进入公共领域 的。 而公众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而进入公共领域的, 他们所讨论的是公共问题。 当然, 这两者之间也是 密切相关的。 大众常常以公众的形式出现, 而公众也必须有大众的基础。 当然, 要深入理解这两个概 念, 还必须进一步分析 “大众性” (Popularit覿t ) 和 “公共性” (Publizit覿t ) 这两个相关概念。 按照弗雷 泽的分析, 公共性具有如下四个含义: 与国家有关的; 所有人都可以进入; 与所有人有关的; 与共同的 善或者共享利益有关。 [3] (P71) 此外,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 公共性意味着一种理性的赞同。 哈贝马斯所说的 公共性主要是指后面三个方面的意思。 而大众性, 则有如下几方面的意思: 与大量的人口有关的; 许多 人共同感兴趣的或满足许多人的利益的; 盲目地随大流的。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 大众性和公共性在一定 程度上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他说, “大众性并不等于公共性, 但是没有公共性, 大众性也不能长久地 维持下去。” [2] (P251) 这是因为, 大众性和公共性一样都和人们的共同利益有关。 如果某种东西不能满足人 们的共同利益, 那么大众也不会赞同。 但是公共性和大众性不同, 公共性是在人们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上 形成的 , 而大众 性是在满足人们 的心理需 要的基 础上 形成的 。 在 谈到公共 性 的时 候 , 哈贝马斯 指 出 , “本来意义上的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 这倒不是因为有了公共性, 每个人一般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 其个人倾向、 愿望和信念—— —即意见; 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共舆论时, 公共性才 能实现。” [2](P252) (译文略改) 我们甚至可以简单地说, 公共性是在人们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认 同, 而大众性不过是人们之间的一种情感上的共鸣。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 态斗争实际上就是获取人们情感上的共鸣的斗争。 为了获得大众在情感上的共鸣, 不同利益集团都会操 纵公共舆论, 制造公共性。 而这种制造的公共性就是大众性。 如果我们把哈贝马斯对于公共性和大众性的区分运用于意识形态的讨论, 那么我们可以说不同的利 益群体为了获得大众的赞同, 会在公共领域进行公开的利益斗争。 比如不同的党派为了获得选举的胜利 而操弄舆论, 这就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斗争。 而在公共领域中探索真理, 寻求有效的社会规范, 这就是 为了理性共识而斗争。 而在为理性共识而斗争的过程中, 不同的社会阶层, 不同的团体会在公共领域为 自己的利益辩护, 提供理由。 在这里, 他们必须说明自己的利益也是全社会的普遍利益, 这种利益具有 公共性。 他们所提出的理由, 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也是意识形态, 但这是一种弱意识形态。 在意识形态斗 争中, 人们常常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 一种策略是激进的斗争策略, 一种是巧妙的辩护策略。 激进的斗 争策略表现为, 把一切理性共识都说成是意识形态, 把弱意识形态转变为强意识形态。 比如, 人们把那 种诉诸人性的观念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并把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说成是进行文化上的渗透 或者是和平演变的手段。 一般来说, 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 在揭露其他社会集团的伪装的时候, 我们采 取这样的策略。 巧妙的辩护策略则表现为, 把少数人的利益打扮成大多数人的利益, 把多数人的利益伪 装成为普遍的利益。 或者说, 把强意识形态演变为弱意识形态, 把弱意识形态演变为理性共识。 它是用 来迷惑大多数人的。 一般来说, 在为自己的利益辩护或者争取大多数人的赞同的时候, 人们会采取这种 意识形态斗争的策略。 这两种策略在实施过程中还会有一些语言上的技巧。 在实施辩护策略的时候, 人 们一般会使用最抽象、 因而涵盖面最宽泛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例如, 把政党的利益说成是 “人民 的利益”。 反过来, 斗争的策略就是揭示宽泛的概念背后所隐藏着的少数人的利益 , 比如, 指出 “人民 利益” 背后的政党利益。 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 人们不仅会有语言上的策略, 而且还要有其他的策略。 从哈贝马斯对于妥协的谈判、 政治伦理的谈判以及道德商谈的区分中, 我们实际上也可以看到, 意识形 态斗争所可能采取的策略。 一些人会在妥协的谈判中使用政治伦理的理由为自己或者自己所代表的利益 集团辩护。 他们从国家或者民族利益的高度来为自己的利益辩护。 在国际政治的斗争中, 一些人会从全 人类的共同道德规范的角度来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辩护。 反过来, 一些人也会指出全人类的共同道德规范 或者普世价值所体现的不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而是少数国家赞同的价值标准。 一些人会指出, 那些所 谓的民族利益实际上不过是少数人的利益。 意识形态斗争实际上就是要灵活地使用妥协的谈判、 政治伦 - 20 - 理的商谈以及道德的商谈中的理由。 在意识形态斗争中, 无论采取哪一种斗争策略, 人们都是在公共领域采取说理的方法来进行斗争。 为自己利益辩护的人, 总是要借助于各种理由说明自己的利益代表了所有人的利益 (是理性共识), 或 者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是弱意识形态)。 但是, 任何人或者利益集团都不能依靠公开的收买或者公 开的勒索来迫使其他人认同自己的理由。 而公开的收买和勒索恰恰是意识形态斗争中最忌讳的方法。 一 旦公开的勒索和收买被实施, 那么所有的说理都会失去其原有的作用。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恰恰就采用了 说理的方式来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分析正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意 识形态斗争中, 说理方式的重要性, 而意识形态上的操纵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所采取 的新策略。 这种策略在有效性上显然比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意识形态策略要逊色得多。 哈贝马斯在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一书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这种意识形态斗争形式。 市场 民主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民主制度。 在这种民主制度中, 选民不是公共领域的参与者, 而是大众, 是选举 “竞争各方的战利品”。 [4] (P365) 哈贝马斯说: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 松散的选民组织越来越让位给真正意 义上的政党—— —它们拥有超地区的组织, 设有官僚机制, 意识形态保持整合, 并对广大选民进行政治动 员。” [2] (P237) 这些政党的主要任务就是争取选民。 他们要制造舆论, 组织活动, [2] (P243) 从而进行启蒙和控制, 教育和操纵。 这些政党要通过控制舆论工具来控制选民。 因此, “对于这些政党来说, 关键问题是谁控 制了强制手段和教育手段, 通过展示或者操纵去影响民众的投票活动。 政党是政治意志形成的工具, 但 是, 它们并不掌握在公众手中, 而是掌握在操纵政党机器的人手中。” [2] (P238) 通过这种操纵了的选举, 某 个政党赢得了政治权力, 它获得了大众的认同, 但是这种认同却缺乏理性的基础。 在哈贝马斯看来, 正 是选举中的操纵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失去了合法性。 在选举中, 他们或者揭露对手, 或者为自己的利 益辩护, 从而争取大众的认同。 [ 参考文献] [1] 哈贝马斯 . 公共领域 [A] . 文化与公共性 [C] .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2] 哈贝马斯 .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M]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3] Nancy Fraser.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J] . Social Text, No. 25/26 , 1990. —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 [M] .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4] 哈贝马斯 .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5] John B. Thompson. The Theory of the Public Sphere [J] . Theory Culture Society, 1993 , (10 ). [6] Pauline Johnson. Habermas ’s Search for Public Sphere [J] .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001 , (4 ). [7] Hans Verstraeten. The Me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for a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ublic Sphere [J] .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 1996 , (11 ). 责任编辑:罗 苹 - 2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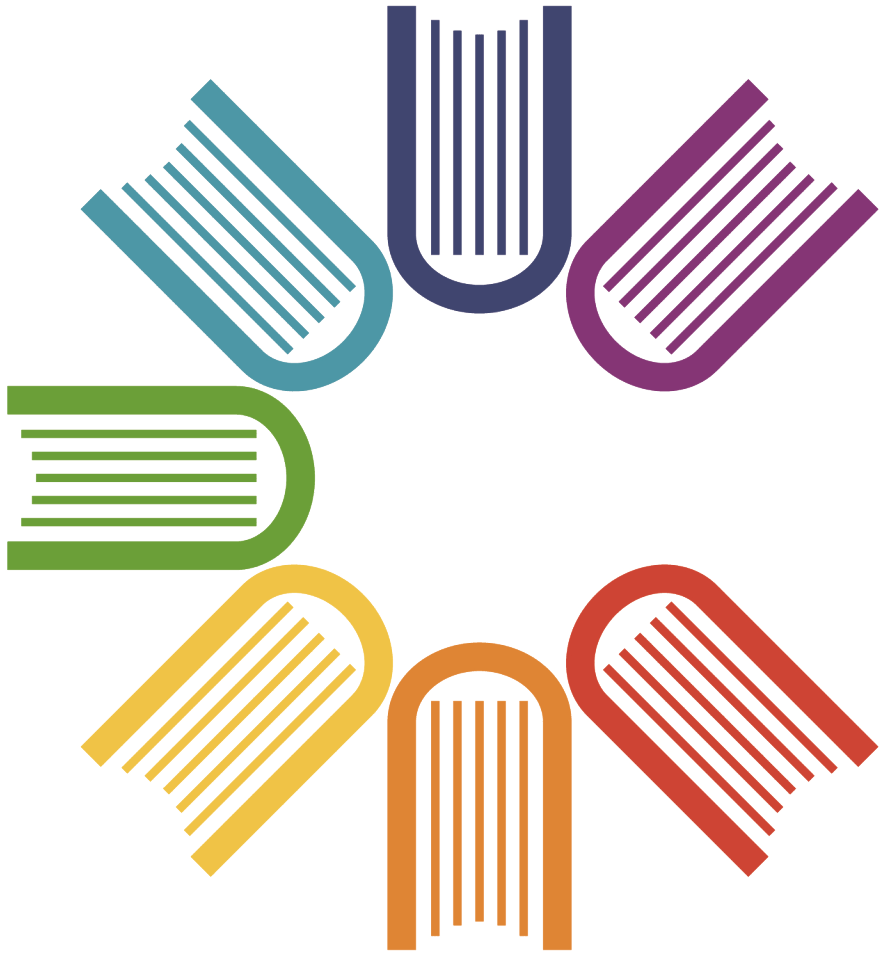
 点击查看:强意识形态、弱意识形态与理性共识.pdf
点击查看:强意识形态、弱意识形态与理性共识.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