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pdf
2014 年第 2 期 安全理论 ህࢴᅐݨखࣴქअሼ* ——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 唐世平 【内容提要】 四个内部维度(即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以及一个外部维 度(即外部环境)对于我们理解他人的行为是必不可少的。不确定性在其中的任 一维度内均发挥着作用。作者构建了一种新的行为归因理论,认为不确定性的五 个维度不仅能各自独立地给人们的认知造成不同困难,而且它们之间的互动也对 人们的认知构成了更加难以应对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这种认知挑战在冲突情境 与合作情境中的表现是有所区别的。缺乏对这些不同的、并且能够互相影响的挑 战的认识已然对国际关系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把握好这五个维度,了解人 们在理解它们时易于出现的各种偏差,对于理解国家在合作或冲突情境中的行为 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文章的理论框架还指向一些特定的假说,而这些假说可以通 过经验与实验方法加以验证。 【关键词】 归因理论;不确定性;认知;国际安全;合作与冲突 【作者简介】 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 授(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D81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74X(2014)020003-39 * 这篇文章更早的版本是笔者2009年9月3-6日于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美国政治科学协会 (APSA)年会上宣读的论文。由衷感谢布莱恩•拉斯本(Brain Rathbun)教授,他与笔者关于不 确定性的激烈而充满成效的讨论促使了这篇文章的诞生,同时也正是他邀请笔者参与了APSA的讨 论。感谢安迪•基德(Andy Kydd)、吴澄秋、尹继武和几位匿名评审人所提出的宝贵意见。本研 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际战略的分析框架与分析工具研究”(项目号12BZZ053)、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历史中的战略行为:美国 和其他国家的比较”(项目号11JJD810017)的支持。本文的英文版参见Tang Shiping, “Outline of a New Theory of Attribution in IR: Dimensions of Uncertainty and Their Cognitive Challenge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3 (September 2012), pp. 299-338。本文中文版是在复旦大 学张旻翻译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江波和方鹿敏两位同学也付出了辛勤劳动。 ·3·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 前言 不确定性,或者说“信息的不完全性” (incomplete information) ,是这个世界 的一个基本事实。它让我们在生活中时不时得经历点儿令人哭笑不得的挫败,却 又让我们的生活因这种挫败而充满了戏剧性。 因此,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不确定 性在包括国际政治在内的社会科学中一直占据着中心位置。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确定性并不只是一个囊括我们所有无知的术语。恰好 相反,对于政治家和国际关系学者来说,不确定性构成了一个永恒却又迫在眉睫 的挑战——如何理解国家某一行为(或者非行为)的直接和深层诱因。政治家们 通常都乐于依赖他们的直觉来揣测他国行为背后的驱动力,而国际关系学者则试 图引入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来构建理解国家行为的框架。 不幸的是,关于行为 归因的社会心理学文献对于理解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的借鉴作用是有限的,因 此,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归因的现有讨论存在着严重不足。 ① 本文试图为国际关系领域构建一个新的归因理论,以此来推动国际关系学科 对不确定性和归因问题的探讨。② 首先,强调不确定性问题有几个不同的维度,而 各维度的不确定性给我们的认知带来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差异的。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在认知这些维度时,我们的心理机制使我们容易产生一些重要的偏差,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次,强调这些维度之间的 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组成的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系统效应(system effects) ① 参见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ap. 3; Stephen G. Brooks,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3 (Summer 1997), pp. 445-477;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Summer 1995), pp. 379-414; Andrew Kydd, “Sheep in Sheep’s Clothing: Why Security Seekers Do Not Fight Each Other,” Security Studies, Vol. 7, No. 1 (Fall 1997), pp. 114-155;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David M. Edelstein, “Managing Uncertainty: Beliefs about Intentions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1 (Autumn 2002), pp. 1-40; Robert Powell, “War as a Commitment Probl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0, No. 2 (Winter 2006), pp. 169-203; Brian C. Rathbun, “Uncertain About Uncertainty: Understanding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a Crucial Concep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4 (December 2007), pp. 533-557; Shiping Tang, “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3 (September 2008), pp. 451-470。 ② 将此处提及的理论明确限定在国际关系领域内的言下之意是,我们的归因行为在不同领域中 有不同的作用方式(特别是在生存和交配这两个迥然相异的领域)。当然,形成这种领域特殊性的决 定性力量是社会进化。交配时两性之间的归因区别(也涉及一些其他的心理特性)已经在进化心理学 (Evolutionary Psychology)领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4· 2014 年第 2 期 无处不在。① 由于我们的大脑没有被赋予系统性思维的天赋,这些系统效应给我们 的认知带来更为艰巨的挑战。② 更重要的是,在不同情境下,这些维度和它们之间 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认知挑战可能是不同的。在国际政治领域,冲突情境和合作 情境中的认知挑战就有所差异。国际关系研究中鲜有涉及对这些相异且相互作用 的维度以及它们单独或者相互作用所造成的挑战的评估,而这种缺位已然给既有 的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许多的困惑。 在深入分析之前,笔者需要做几项重要的说明。首先,本文的理论框架指向 一些特定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可以通过经验与实验方法加以验证。本文是构建理 论(详见表 1 的概括)迈出的第一步。尽管文中提供了一些来自国际关系和社会 心理学领域的证据,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花絮性的论证。 表1 国际关系新的归因理论框架 项目 情境 冲突关系(无论是否 模棱两可(可以向任 合作关系 / 建立合作 存在现实的冲突) 何一个方向演变) 能力 当一方的权力远高于另一方时,我们有可能 通常,我们倾向于低 低估另一方的能力。否则(即当我们的权力 估别人能够贡献于集 与他国大致相当或低于另一方时), 我们倾向 体利益的能力。 于会高估他国的能力。 决心 当关系模棱两可时, 我们倾向于低估另一 类似于我们对另一方 我们倾向于忽视这一 方 遵 守 其 协 定 的 决 能力的估计。 维度。 心。 利益 我们倾向于否定、忽视、降低或非法化另一方的利益。 意图 我们倾向于夸大另一方的恶意,且同时低估另一方的善意。 外部环境 当另一方的行为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倾向于强调其所面临的外部 限制:他们表现良好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么做;而当他国的行为不 符合我们的期待时,我们常常弱化其所面临的外部限制:他国表现 得不好是因为他们天性本恶。 我们处理不确定性的一般倾向会助长冲突而阻碍合作。 其次,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国际关系,所以笔者将群体内(in-group)和群体间 ① 参见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② 参见A. K. Shah and D. M. Oppenheimer, “Heuristics Made Easy: An Effort-Reduction Framewor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34, No. 2 (March 2008), pp. 207-222; Gerd Gigerenzer and Daniel G. Goldstein, “Reasoning the Fast and Frugal Way: 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103, No. 4 (October 1996), pp. 650-669. ·5·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 (out-group)的认同作为下文讨论中的预设条件。假定在进化历程中,经历过长期 “我们”和“他们”的对抗(us-versus-them)的个体,已然将固定了的对内和对 外群体认同完全地加以内化。群体认同在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中尤其突 显,其深刻地塑造我们对其他个体和群体的看法、态度及行为,而塑造的依据是 判断那些对象是属于我们所认知的群体内部,还是群体外部。① 再次,尽管笔者的分析暗含了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根据个体间互动来推断出群 体间互动的意味,但已深刻意识到“个体间和群体间的不连续性”(interpersonalintergroup discontunity)的存在,② 并且理解个体与群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 然两者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 ③ 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拒绝使用单纯的个体主义 (individualism)研究路径来探讨群体间关系问题,而这种研究路径往往是“理性 选择” (Rational Choice)流派的理论家们所拥护的。笔者引用个体间层次的研究, 仅仅是因为个体间层次的某些经验能够在群体层次上得以沿用。就像越来越多的 社会心理学家认识到的那样,未来的研究不应该再拘泥于个体与群体的二分法, 而是应该在分析个体的决策行为时将其置于群体的背景之中加以考虑。这一点也 是笔者所提倡的。 ④ 最后,虽然本文将关注点放在了由不确定性带来的认知挑战上,但需要明确 强调的是,除了心理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政治、预算和战略因素)也 (Motivated Biases)。 会让我们的认知误入歧途,从而造成所谓的“诱发性偏见” 这些诱发因素,通常能够与笔者在这里讨论的心理性偏见相互作用,从而又为我 们理解他国的行为增添了一层挑战。为了便于分析,这里笔者只关注那些由不确 定性本身所带来的心理性挑战。 文章余下的部分结构如下。在对理解他国行为的不确定性的五个主要维度进 ① 参见Robert A. LeVine and Donald T. Campbell, Ethnocentrism: Theories of Conflict, Ethnic Attitudes, and Group Behavior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72; Henri Tajfel,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Marilyn B. Brewer, “The Role of Ethnocentrism in Intergroup Conflict,” in S. Worchel and W. G. Austin,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icago: Nelson-Hall, 1986; J. C. Turner, M. A. Hogg, P. J. Oakes, S. D. Reicher and M. S. Wetherell,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② Tim Wildschut and Chester A. Insko, “Explanations of Interindividual-Intergroup Discontinuity: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8, No.1 (2007), pp. 175-211. ③ 参见David L. Hamilton and Steven J. Sherman, “Perceiving Persons and Groups,”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10, No. 2 (1996), pp. 336-355; Robert P. Abelson, Nilanjana Dasgupta, Jaihyun Park and Mahzarin R. Banaji, “Perceptions of the Collective Othe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2, No. 4 (August 1998), pp. 243-250. ④ Ivan D. Steiner, “Paradigms and Groups,” in Leonard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0,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86, pp. 173-220. ·6· 2014 年第 2 期 行描述之后,第二部分指出国际关系和社会心理学中现有的归因理论研究并不足以 帮助我们理解他人的行为 ;第三部分着重分析由这些维度带来的普遍性挑战 ;第 四部分强调了这些维度在不同情境中带来的不同挑战在冲突情境和合作情境中, 我们对他国行为的解释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性 ;第五部分从心理学和国际关系学 的研究文献中提取了一些证据,用以说明我们在归因时常常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 第六部分讨论我们无法正确认知事物所带来的后果 ;第七部分抽提出理论意义。 最后是简要的结论。 一 不确定性与国际关系中归因理论的不足 不确定性的主要维度可以分为两个更宽泛的类别 :内部维度和外部维度。 ① 内部维度包含四个维度,即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冲突 关系或一场整体性冲突中的总体战争能力,或者指一个国家在局部冲突中的即时 作战能力。然而在合作情境下,一个国家的能力由其所能提供的帮助 (比如在军事、 财政和医疗上的帮助)来衡量。决心是指实现承诺的意志,这里的承诺可以是冲 突情境中发出的威胁,也可以是合作情境下愿意做出的贡献。一个行为者的意图 是指实现目标的战略偏好。② 在国际关系的相关讨论中,我们通常把意图分为两大 类 :善意的或是恶意的。一个国家如果故意威胁他国,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恶意的, 反之则是善意的。③ 一个行为者的利益即是他的目标。这个目标既可以是当下的,也可以是长期 的。所以,利益就是指一个行为者对于结果的偏好。④ 由于动机是指“促成一个人 以特定方式行动的驱动力” ,或是“激发行为的一种情感、愿望、生理需求或其他 诸如此类的冲动”,⑤ 我们时常把一个行动者的即期利益称作他的动机,或者干脆 ① 除了这里重点强调的五个维度之外,国际关系领域中还存在与不确定性相关的一些其他概念,如 声誉(Reputation)、可信度(Credibility)、信用(Trustworthiness)等。对这些概念,本文不予讨论。 ②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48-49; Robert Powell,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Neorealist-Neoliberal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Spring 1994), pp. 313-344. ③ 参见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10, Chap. 1。 ④ Robert Powell,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Neorealist-Neoliberal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Spring 1994), pp. 313-344. ⑤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83, p. 447; Online Farlex Dictionary, 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motive. ·7·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 把动机等同于利益。① 在强调结构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追求的抽象目标涵盖了 安全、权力、满意度(Satisfaction)和威望(Prestige)等。②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 国家不仅追求诸如领土、财政收入、表决权(一般在国际组织中)之类的有形目标, 而且还力图实现那些无形且难以捉摸的目的,比如荣誉、威望、声誉以及可信度。 我们通常为国家行为的外部维度贴上“外部环境”或是“战略环境”的标签。 在这样的标签下,我们把国家边界以外的因素笼统地归结在一起,而这些因素可 能囊括了一个国家的地缘环境、其在区域内或在整个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同 盟国的有无与强弱、敌对国的强弱等。整个国际体系的特性(即各种不同意义上 的无政府状态)和国际政治演变的主流趋势(如全球化)亦构成了国家运转所处 的外部环境的关键维度。 了解他国行为背后的能力、利益(动机) 、意图、决心以及外部环境,是一个 归因和认知的过程。毫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家们已经热衷 于将社会心理学中对归因和认知问题的研究成果引入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对归 因和认知理论的首次引入由罗伯特 • 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其最负盛名的《国 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中加以完成。③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是社会心理学中归因研究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 诞生了该领域中最著名的一批著作和标签,例如“基本归因误差”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简称 FAE)。④ 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归因理论的引入都建立 在这些早期著作的基础上。然而,正如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早 ① 参见Charles L. Glas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2 (July 1992), pp. 497-538; Evan Braden Montgomery, “Breaking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Realism, Reassurance, and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2 (Fall 2006), pp. 151-185。 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ion-Wesley, 1979;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 50-90;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③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参见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Janice Gross Stein, “Building Politics into Psychology: The Misperception of Threat,”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9, No. 2 (June 1988), pp. 245-271;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④ 在这方面有一些不错的综述性论著,参见Edward E. Jones and Richard E. Nisbett, “The Actor and the Observer: Divergent Perceptions of the Causes of Behavior,” in Edward Jones, et al., eds., Attribution: Perceiving the Causes of Behavior, Morristown: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2, pp. 79-94; Harold H. Kelley and John Michela, “Attribu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31 (1980), pp. 457501; Daniel T. Gilbert and Patrick S. Malone, “The Correspondence Bia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17, No. 1 (1995), pp. 21-38。 ·8· 2014 年第 2 期 期的归因理论著作存在着严重的概念性错误与操作性问题。① 实际上,就如贝特伦 • 马勒(Bertram F. Malle)所敏锐指出的,许多现有的主流归因研究文献甚至没有提 及那些解释行为的挑战本身。② 它们把归因(即把行为当做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结 果来解释)和解释社会结果混为一谈,尽管这两个任务除了一些表面的相似点之 外其实有本质的区别。③ 更糟糕的是,即便它们提到了归因,也往往把归因看成是 一项用(内部的 / 属性的)特性或者(外部的 / 情境的)因素来解释行为的任务。 在近期的研究中,马勒和他的同事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归因理论。④ 马勒的新理 论首次把行为划分为两大类: 故意行为(Intentional)和非故意行为(Unintentional) 。 对于非故意行为(比如说本能行为) ,我们的解释是直截了当的 :我们仅仅声明导 致行为的原因(Cause) ,并不去做更深入的探究。对于故意行为,我们的归因可以 (Reason Explanation)和“带因果历史的原由” (Causal 被归纳为两个模式: “原由解释” History of Reason) 。前者可以被理解为表层归因,我们仅仅陈述他人行为的代理原 因(Proxy Reason);后者是更为复杂、或者说是更为深层的归因,我们对导致一 个人行为的原因做进一步回溯,并且把个人经历和文化因素都纳入到解释中去。⑤ 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关注那些故意行为。这是因为与 时常受本能影响的个体不同,国家并不会遵循本能来行动。此外,我们大多同时 采用表层与深层归因来解释他国行为。因此,社会心理学中归因理论的最新进展 或许为国际关系学者提供了更多前景。不过,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即使有这 些最新进展,⑥ 社会心理学中的现有归因研究至少存在着两大关键的不足。 ① 参见Daniel T. Gilbert and Patrick S. Malone, “The Correspondence Bia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17, No. 1 (1995), pp. 21-38; John Sabini, Michael Siepmann and Julia Stein, “Target Article: The Really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sychological Inquiry, Vol. 12, No. 1 (2001), pp. 1-15. ② Bertram F. Malle, How the Mind Explains Behavior: Folk Explanations, Meaning, and Social Interac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2004, pp. 5-27. ③ 在此之后,“归因”即意指“解释行为”。 ④ Bertram F. Malle, “How People Explain Behavior: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3, No. 1 (February 1999), pp. 23-48; Bertram F. Malle, How the Mind Explains Behavior: Folk Explanations, Meaning, and Social Interaction; Bertram F. Malle, “Attributions as Behavior Explanations: Toward a New Theory,” in D. Chadee and J. Hunter, eds., Current Themes and Perspectives in Social Psychology, St. Augustine: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2007, pp. 3-26. ⑤ Bertram F. Malle, How the Mind Explains Behavior: Folk Explanations, Meaning, and Social Interaction, Chap. 4. 马勒的理论实际上界定了解释故意行为的第三种模式,即“促成因素解释” (Enabling Factor Explanations)(pp. 109-111) 。根据本文的理论观点,这种“促成因素”模式不是一 种独立的归因模式,因为所有归因行为都暗示、甚至明示地假定了一个故意行为背后存在某些“促成 因素”。此外,虽然马勒的理论非常复杂精妙,但是他的讨论过多地集中于语言学层面,因而远远脱 离了现实世界中的国际关系情境。 ⑥ 参见Bertram F. Malle, How the Mind Explains Behavior: Folk Explanations, Meaning, and Social Interaction。 ·9·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 第一,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用两种互有重叠的二分法来区分导致他人行 为的可能原因,即“属性原因” (dispositional)和“情境原因” (situational) 、内部(或 者个人)原因和外部原因。① 尽管许多人把内部原因等同于属性原因,外部原因等 同于情境原因,② 但这两种二分法并不完全重叠。例如,一个国家也许有一个脆弱 的政体,这是内部原因。然而严格来说,这种情况是情境的而不是属性的。实际上, 尽管爱德华 • 琼斯(Edward E. Jones)和基思 • 戴维斯(Keith E. Davis)③ 把意图(实 际上他们指的是动机 / 利益和意图)看成是属性的, 但这在大多数情形下并不正确, 因为众所周知行为者的动机 / 利益和意图可能会变化。因此,不是所有的内部原因 都是属性原因。 与此同时,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属于外部原因,但在领土国家时代,该环境 更接近于属性原因。因此,尽管大多数外部原因不是属性原因,但并非所有的外 部原因都是情境原因。所以,即便只是作为启发式(heuristic)的工具,属性 / 情 境这种二分法在行为归因上的运用从本质上来说也是无效的。而相对的,内部 / 外 部二分法则应当被更多地使用。④ 毕竟,在严格意义上几乎不存在完全属于属性的 原因——绝大多数原因都是情境的。 此外,即使采用了内部 / 外部的二分法,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研究也只为理 解国际政治提供了有限的帮助。这是因为内部 / 外部二分法对于理解行为者的行为 来说太过粗糙。实际上,社会心理学家经常把动机(目标 / 利益)和意图均视为意 图,⑤ 而把行为者的能力、决心和外部限制统归为“促成因素”。⑥ 然而,作为国 ① 除了这两种二分法之外,还有由伯纳德•韦纳(Bernard Weiner)所引入的“稳定原因和不稳定 原因”这种二分法。笔者忽略此种二分法是因为它与群际(Intergroup)关系不太相关。 ② 参见Glenn D. Reeder and Marilynn B. Brewer, “A Schematic Model of 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 in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86, No. 1 (Janunary 1979), p. 61;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③ Edward E. Jones and Keith E. Davis, “From Acts to Dispositions: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in Person Perception,”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65, pp. 219-266. ④ Bertram F. Malle, “How People Explain Behavior: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3, No. 1 (February 1999) , pp. 23-48; John Sabini, Michael Siepmann, and Julia Stein, “Target Article: The Really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sychological Inquiry, Vol. 12, No. 1 (2001), pp. 1-15.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罗伯特•杰维斯采用“外部/内部”二分法(参 见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 2),而乔纳森•默瑟则采用 “属性 / 情境”二分法(参见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 2.)。 ⑤ Edward E. Jones and Keith E Davis, “From Acts to Dispositions: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in Person Perception,”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pp. 219-266. ⑥ Bertram F. Malle, How the Mind Explains Behavior: Folk Explanations, Meaning, and Social Interaction; Bertram F. Malle, “Attributions as Behavior Explanations: Toward a New Theor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Oregon, 2003, pp. 3-26. · 10 · 2014 年第 2 期 际关系学者,即使我们不得不把许多维度简单地囊括在“外部 / 战略环境” (External/ Strategic Environment)的标签下(当然这种做法并不令人满意), 我们也必须把“内 部原因”划分为四个维度,因为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对于理解他人战略行为 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同样也是比较根本的一点,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研究极少涉及群体动态 (Group Dynamics)。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个体主义作为一种范式已经在社会心理 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① 因此,尽管“极小群体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 明确认为群体动态具有非常强健的作用,② 但大部分归因理论家都趋向于忽视群体 动态对归因的影响,就连那些最新的研究也不例外。③ 然而, 国际关系中的归因几乎是永恒地被笼罩在群体动态的魔咒之下。实际上, 社会心理学自身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来证明通常在极小群体(Minimal Group) 存在的情况下,④ 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和归因的相互作用会加剧归因误 差或偏见并使其更为固化而难以被矫正,由此产生了托马斯 • 佩蒂格鲁(Thomas F. Pettigrew)所谓的“终极归因误差” (The Ultimate Attribution Error) 。⑤ 在现实世界的 国际政治中,族群中心主义(表现为种族中心和群体认同)常常与归因携手而来。⑥ 因此,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拒绝纯粹的个体主义研究路径,转而按照群体动态(主 ① Ivan D. Steiner, “Paradigms and Groups,” in Leonard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pp. 173-220. ② Henri Tajfel,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Henri Tajfel and John C. Turner,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W. Worchel and W. G. Austin, William,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icago: Nelson-Hall, 1986, pp. 7-24. ③ Bertram F. Malle, “How People Explain Behavior: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3, No. 1 (February 1999), pp. 23-48; Bertram F. Malle, How the Mind Explains Behavior: Folk Explanations, Meaning, and Social Interaction; Bertram F. Malle, “Attributions as Behavior Explanations,” pp. 3-26; John Sabini, Michael Siepmann, and Julia Stein, “Target Article: The Really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sychological Inquiry, Vol. 12, No. 1 (2001), pp. 1-15. ④ 因为族群中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群体层次的自我中心主义。我们每个人都是族群中心的(或民 族-国家中心的),区别只在于程度不同。 ⑤ Thomas F. Pettigrew, “The Ultimate Attribution Error: Extending Allport’s Cognitive Analysis of Prejudi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5, No. 4 (October 1979), pp. 461-476; Miles Hewstone, “The ‘Ultimate Attribution Error’?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Intergroup Causal Attribu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0, No. 4 (July/August1990), pp. 311-336. ⑥ Donald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 2. · 11 ·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 要是族群中心主义)来理解国际关系中的归因是势在必行的。① 正如即将在下文中 明确揭示的那样,族群中心主义普遍而深远地影响着我们对于他人行为的归因。在 国际关系领域中,不考虑族群中心主义就无法把握归因问题。 因此,仅仅利用现有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远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之复杂性。 国际关系学者应当超越社会心理学对归因的认识,本文正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 步。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对国际关系研究和社会心理学研究有所贡献。 二 对人们认知的普遍性挑战 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给人们的认知带来了众多的挑战。这些挑战可以被理解 为分属于三个层次。前两个层次是普遍性的,而第三个层次则是情境性的。这一 部分讨论的是普遍性挑战,情境性挑战将在后文中予以介绍。 (一)普遍性挑战 :单维度的挑战 在不确定性的四个内部维度中,能力维度可能是最容易观察的。两个互有关 联的原因导致了这一点。第一,尽管错误估计别人能力的事情时有发生,但能力 更容易被观测到。第二,相对于利益以及意图来说,能力的变化是缓慢的。行动 者需要时间来建立和累积起自己的能力,而其意图与利益却可能在一夕之间就发 生改变。这一事实给了他国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一个行动者变化的能力。 一般说来,对于他国决心的不确定性只有当我们已经和其他行为者处于冲突 或者合作的情境中时才会变得重要 :除非我们想和他们合作或者是反对他们,我 们通常不会去考虑别人的决心。决心对我们的认知造成的困难比能力更多,但比 意图和利益要少。由于决心通常是能力的一个函数(函数中还要加上利益、意图 和外部环境) ,决心不像利益和意图那样容易改变。不过, 正如理查德 • 勒博(Richard Ned Lebow) ② 所强调的,由于其他一些心理因素的影响(比如由他人行为引发的 愤怒和憎恨),决心比能力要容易改变。 一个恶意国家(Malignant State)不会真正在意他国的意图。然而对于一个善 意国家(Benign State)而言,自其致力于制定一个针对他国的完善的安全战略开始, ①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0. 事实上,琼斯和哈里斯证明基本归因误差的首个实验包含着一个十分明显的群体动 态:实验对象按计划将从他人所写的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文章中归因出撰写这些文 章背后的动机,而这个实验的时间正好是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之后不久。参见Edward E. Jones and Victor A. Harris, “The Attribution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3, No. 1 (January 1967), pp. 1-24。 ②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2 · 2014 年第 2 期 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就会带来麻烦。善意的国家如果错误地把一个恶意国家当做 善意国家,那么就有被恶意国家利用的风险。相反,如果善意国家把另一个善意 国家误认为恶意国家,将可能使两国间的安全困境进一步恶化,最终以不必要的 军备竞赛和冲突收场。① 更为关键的是,解读他人的意图比评估他人的决心更困难: 它需要耐心地传递保证信号并解读他人对这一保证姿态的回应。② 此外,意图能够 比能力和决心改变得更快。鉴于此,对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造成的问题是独一无 二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意图的不确定性会在国际关系领域处于中心位置。③ 他国的利益也许是第二容易被觉察到的,因为大多数国家认为他国生死攸关 与核心的利益(比如说领土完整)是不证自明的。然而,我们对他国利益的评价 (尤其是那些核心利益之外的部分)面临严重的双重标准问题。④ 大部分是由于我 们的族群中心主义,我们趋向于合法化、甚至美化自己的利益和自己对利益的追 求,同时非法化他国的利益和他国对利益的追求。因而,我们把自己的利益看成 是合法的、克制的和适度的,却把他国的利益看成是非法的、野心的和贪婪的。 我们同样认为自身利益之于自身,相比他国利益之于他国来得更为关键、甚至更 为生死攸关。由此,我们把自己对利益的追求看成是文明的、以维持现状为导向 的、正义的、思虑周详的、与人为善的,而把他国对利益的追求看成是不文明的、 修正主义的、非正义的,贪婪成性的和具有侵略性的。 除此之外,我们通常把我们的荣誉、威望、声誉和权力看成是合法利益,却 很少把他人的荣誉、威望、声誉和权力看做是合法的。更有甚者,我们倾向于收 回我们的沉没成本(Sunk Cost,例如流出的血汗、赌上的声誉、倾注的荣耀) ,而 ①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 3;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 Andrew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ps. 2 and 3;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Chap. 4. ② Andrew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s. 7 and 8;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Chap. 5. ③ Shiping Tang, “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3 (September 2008). ④ S. Oskamp, “Attitudes toward U.S. and Russian Actions: a Double Standard,” Psychological Reports, Vol. 16 (February 1965), pp. 43-46; Richard D. Ashmore, David Bird, Frances K. del Boca, and Robert C. Vanderet,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Double Standard in the Per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olitical Behaviors, Vol. 1, No. 2 (Summer 1979), pp. 123-135; Ifat Maoz, Andrew Ward, Michael Katz and Lee Ross, “Reactive Devaluation of an ‘Israeli’ vs. ‘Palestinian’ Peace Proposal,”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 4 (August 2002), pp. 515-546. · 13 ·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 任何微小的收获都会被当做是需要守卫的所有品。① 然而,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 却极少把他国的沉没成本以及新的收获看作需要防卫的新利益。简言之,政治家 们的族群中心主义偏见使他们强烈缺乏移情能力(Empathy) 。② 总的来说,在理解他国的利益时,我们的思维是严重的“双重标准”的。这 种双重标准在冲突情境与合作情境中均适用,但在前者中表现得更强烈。③ 外部环境则相当之复杂。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即使是仅仅评估我们自身的外 部环境就已经是个足以令人怯步的挑战,更不用说去评估他国所处的外部环境了。 更糟糕的是,由于倾向于以省力模式(Effort-Saving Mode)来运行,④ 我们的大脑 习惯用过于简单的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 (二)普遍性挑战 :系统和动态效应 不确定性的五个维度的运作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静态的。它们持续地互动 并形成一个动态的系统 :不同维度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并且能够彼此相互改变。 能力的变化通常会改变对利益的界定 :能力越大,利益的界定就越具扩张性, 或者说更为野心勃勃,能力越小则相反。换句话说,如杰维斯⑤ 早先所言,我们倾 向于把我们处理不了的事情放到一边,而老是想着那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或者 说我们自认为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 。这一长期被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观念 至少道出了部分真相。 目 标 或 利 益 的 变 化 时 常 导 致 战 略 偏 好 的 改 变, 用 马 基 雅 维 利(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 的 话 来 说, 就 是“ 目 的 是 手 段 的 理 由 ” (Ends Justify Means) 。更具有扩张性的目标,通常需要更为无畏且更具侵略性的战略。而意图 的变化也会推动能力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表现在总体军事实力上,还体现为 军事能力的性质。恶意要求更多的进攻性能力,而善意则相反。在希特勒统治下 的德国一直将进攻性军事能力优先于防御性军事能力发展,然而英国和法国的做 ① 这种动态与前景理论(Prospect / Framing Theory)所捕捉到的“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 问题有关。参见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 Vol. 47, No. 2 (March 1979), pp. 263-292; 对于国际关系动态与前景理论的文献回顾参见 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1 (March 1997), pp. 87-112。 ② Janice Gross Stein, “Building Politics into Psychology: The Misperception of Threa,”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9, No. 2 (June 1988), pp. 249-251, 253;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09-314. ③ 事实上,双重标准心理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对我们的盟友同样适用(他们仍然是“他者”),尽 管双重标准的程度比针对我们(潜在的)对手的要轻一些。 ④ A. K. Shah and D. M. Oppenheimer, “Heuristics Made Easy: An Effort-Reduction Framewor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34, No. 2 (March 2008), pp. 207-222. ⑤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372-378. · 14 · 2014 年第 2 期 法或多或少与此相反。① 意图和决心同样也能够相互作用 :一个国家偏好于什么样的战略取决于它为 某些目标奋斗的意愿有多大。② 同样,决心是目标、能力、外部环境以及意图的函 数。在希特勒政权相对虚弱的时期(1936 年前后),希特勒在莱茵兰地区再军事化 期间就已经准备好,一旦英国和法国立场坚定就立刻放弃。然而,1938 年后,希 特勒变得更难以被威慑(吓阻),不惜冒更大的风险去实现他的魔鬼计划,因为希 特勒确信他将获胜,并且不断膨胀的野心驱使他在追求目标的道路上变得更加坚 定不移。与此同时,所有四个内部维度都能够单独或共同地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 当一个国家得到盟国支持时,其利益(或者是目标)界定可能会有所扩大,反之 亦然。相类似的,一个国家的(真实或是想象的)能力和由其激发的在危机中的 决心将会被真实或想象中的盟国的支持所支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匈帝国与塞 尔维亚的对峙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威廉二世(Kaiser William II)的空白支票很显 然使奥匈帝国变得更加无所顾忌(也更为野心勃勃)。越南战争期间,越南北方斗 争到底的决心如果没有苏联和中国的支持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当战略机会(比如权力真空)被认为有利时,一个原本善意的国家很可能被 引诱进行扩张(即机会主义扩张) ,由此变成一个恶意国家。③ 如果扩张成功,该 国能力将得到增强,而其不断壮大的能力也将反过来推动其利益界定的扩大,并 继而增强其扩张的决心。 由我们和他国之间的相对权力分配所部分构成的外部环境,不仅是我们和他 国行为的基础,也是国家归因努力的基础。因此,当他国弱于我们时,我们会认 为他们其实并没有合作的意图,他们之所以合作只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而 不是因为他们是善意的 ;当他国的力量等于或者强于我们时,我们则认为他们没 什么兴趣与我们合作,因为他们是恶意的或者至少决意要压榨我们。 同时,一个国家的能力和意图能改变它的外部环境。一个带有恶意而强大的 国家的最后结局是招来更多的敌人,而(或者)唯一的盟友只有那种为了寻得利 ① Douglas Porch, “Military ‘Culture’ and the Fall of France in 1940: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4 (Spring 2000), pp. 157-180. ②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48-49. ③ 需要强调的是机会主义扩张并不是“自动的”。此外,一个机会主义扩张的国家仍然是一个恶意 的国家,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L. Glaser)和杰弗里•托利弗(Jeffery W. Taliaferro)给进行机会主义 扩张的国家贴上“寻求安全国家”(Security-Seeking States)的标签(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意味着善意国 家)是具有误导性的。参见Charles L. Glas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2 (July 1992), pp. 497-538;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 50-90; Jeffer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2000-2001), pp. 152-158。 · 15 ·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 益或保护的随强者。① 一个善意却弱小的国家则很有可能会得到更多同情它的盟 友。在这两者之间还有许多能力适中、意图也并不那么明确的国家,它们的能力 和意图同样也会对外部环境产生一定的塑造作用。 系统效应的另一个方面其实更难以应付 :能力(作为国家实力的一部分)是 国家利益或目标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几乎每个政治家都将权力当做一个(即期) 目标,并且每个人都相信其他人也会这么做。同时,正如上文所言,尽管我们把 自己的沉没成本和新得利益看成是自己的既得利益,我们并不会把他国的沉没成 本和新得利益看成是他们的既得利益。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常忽视权力和利益之 间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影响。 由于这五个维度之间能够彼此相互作用并进而构成了一个系统,它们相互作 用所产生的系统效应并不能单纯地通过把它们相加来评估,而是必须以系统的方 法来测量。 ② 不幸的是,由于常常以“省力模式”来运转,我们的大脑更倾向于以 非系统性的方式去思考。对系统性思考的厌恶感并不只是标准社会心理学研究在 “启发法”(Heuristics)或者是“图式思维”(Schematic Thinking)标题下所捕捉 的那些东西。③ 不确定性的五个维度所产生的系统效应以及我们对于系统性思考的 厌恶,对人们的认知造成的挑战远远比我们认为的要大。 三 人们的认知所面临的不对称的情境挑战 : 冲突情境与合作情境的比较 国际关系领域对归因的理解大部分还停留在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由社会心理 学家所推广的“基本归因误差”的范畴下。“基本归因误差”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倾 向于将更多的属性特征(Dispositional Properties)投射(Project)到他人的行为中, 即便他人的行为是由属性和情境因素所共同驱使的。尽管琼斯和戴维斯④ 在重构弗 里茨 • 海德(Fritz Heider)⑤ 所提命题时认为感知者的归因很大部分受到感知者所 ① Stephen Walt, The Origin of Alli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7. ②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③ Richard E. Nisbett and Lee Ross, Human Inference: Strategies and Shortcomings in Social Judgement,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80. ④ Edward E. Jones and Keith E. Davis, “From Acts to Dispositions: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in Person Perception,”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 pp. 219-266. ⑤ Fritz Heider, “Social Perception and Phenomenal Causa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51, No. 6 (November 1944), pp. 358-374; Fritz Heider,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iley, 1958. · 16 · 2014 年第 2 期 在环境的影响,但是这一关键的洞见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① 社会心理学家们确实 强调了一个行为对行动者和行动的感知者而言是否称心如意构成了感知者归因的 一个关键情境环境。② 然而,他们始终忽略了另一个关键维度 :在现实生活中,除 了所关注的行为是否称心这一点之外,还有关键的一点是塑造我们对于他人行为 的理解,即行动的感知者和行动者是处于(潜在的)冲突性关系或情境中,还是 处于合作性关系或情境中。 在此描绘的新理论再次强调我们自身所处环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于 他人行为背后存在的各类外部限制的相对影响权重的解读。更重要的是,它强调 对于国际关系和我们的社会生活而言,我们最关注的就是情境是冲突性的还是合 作性的。正确判断我们所属的情境对于我们成功地生存和繁衍是至关重要的。 在群体层次,我们最为关心的是我们群体的生存。这种对群体生存的关切使 我们的大脑更容易感知更多危险而非安全,人们的认知在冲突情境与合作情境中 的不同运作方式因而也体现出了这一点(见表 1 中的总结)。换言之,不确定性的 各个维度在合作情境和冲突环境中所造成的挑战是明显不对称的。③ 对于他人的目标和意图,人们的认知从冲突情境到合作情境大体上是一致的。 如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倾向于否定、忽略、贬损和非法化他国的利益,而对我们 自身利益的态度却恰恰相反。 同时,对于意图,不管情境如何,我们都倾向于高估他国的恶意而低估他国 的善意。在个体间与群体间的层次上,最直接的证据表明这种不对称性来自于小 ① 事实上,在对基本归因误差的重要再构中,李•罗斯指出社会心理学家同样也倾向于低估情 境在驱使我们行为方面发挥的作用。参见Lee Ross, “The Intuitive Psychologist and His Shortcomings: Distortions in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② Fritz Heider, “Social Perception and Phenomenal Causa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51, No. 6 (NoVember 1944), pp. 358–374; Fritz Heider,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iley, 1958; Edward E. Jones and Keith E. Davis, “From Acts to Dispositions: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in Person Perception,”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pp. 219-266. 事实上,海德 明确指出了我们的需求会影响我们的归因以及对好的行为和坏的行为、好的行动者和坏的行动者的辨 别。他同时也提及了福康纳(Fauconnet)对(指派)责任的讨论。这一论断立刻指向了一种对我们思 维运行模式的进化解释,尽管其在形式上与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还有所差异。参见 Fritz Heider, “Social Perception and Phenomenal Causa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51, No. 6 (November 1944), pp. 358-361。 ③ 人们的认知是以非对称的方式运作的,这一事实已经在社会心理学中得到牢固确立,并通常以 “错误肯定”(False Positive)与“错误否定”(False Negative)间的不对称性而为人所知。一个与之相 关的现象是广为接受的“负面偏见”(Negativity Bias)现象:负面经历往往要比正面经历在我们的记忆 中表现得更强烈,停留的时间也更长久。相关的文献述评,参见Roy Baumeister, Ellen Bratslavsky, Catrin Finkenauer, and Kathleen D. Vohs, “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Vol. 5, No. 4 (December 2001), pp. 323-370; Paul Rozin and Edward, B. Royzman, “Negativity Bias, Negativity Dominance, and Contag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5, No. 4 (November 2001), pp. 296-320。 · 17 ·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 孩和成人的“敌意 / 险恶归因偏见”(Hostile/Sinister Attribution Bias):我们一般趋 向于把他者的那些会对我们造成妨碍、且由此不令我们称心的行为归因为带有敌 意或险恶意图,纵使这些行为完全是无意的或者至少是没有明确意图的。① “敌意 / 险恶归因偏见”经常以“反应性贬值” (Reactive 在群体间层次上, Devaluation)的形式呈现。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倾向于对他人的让步提议进行反应 性贬值。当对方提出了妥协和让步,老练的谈判者一贯贬低这些妥协让步,判定 这些还不够充分,并且认为这多半是受情境因素(特别是谈判者自身的强硬态度) 驱动而不是对手希望妥协或有意合作。② 当一个实际由以色列人提出的和平提案以 巴勒斯坦提案的名义来呈现给以色列犹太人和亲以色列美国人时,这个提案会被 认为是不利的(即“这个提案会更偏向巴勒斯坦人”);当同一个提案作为以色列 人的提案被呈现给以色列犹太人和亲以色列美国人时,它会被认为是有利和“不 在对抗性的国家间关系中, 偏不倚的”。③ 最后,从现实生活中的国际政治案例来看, 决策者通常把称心的结果(比如妥协)归因于他们自身的努力而把不如意的结果 归因于他人的恶意。杰维斯④ 和德博拉 • 拉森(Deborah W. Larson)⑤ 在他们的研 究中充分地展示了这样的证据。 在冲突情境中,当他国的能力大体同我们的一样或是高于我们时,我们倾向 于高估他国施加伤害的能力。因此,尽管(事后看来)英国和法国在 1938 年以前 与希特勒交战要比一年后再来敷衍了事地打一仗好得多,⑥ 它们仍高估了希特勒德 ① Kenneth A. Dodge, Gregory S. Pettit, Cynthia L. McClaskey and Melissa M. Brown, Social Competence in Children,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Vol. 51 (1986), pp. 1-85; R. M. Kramer, “Paranoid Cognition in Social Systems: Thinking and Acting in the Shadow of Doub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2, No. 4 (November 1998), pp. 251-275; R. M. Kramer and D. M. Messick, “Getting by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Our Enemies: Collective Paranoia and its Rule in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C. Sedikides, J. Schopler and C. A. Insko, eds., Intergroup Cognition and Intergroup Behavior,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8, pp. 233-255. ② Lee Ross and Robert Ward, “Psychological Barriers to Dispute Resolutions,” in Leonard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27,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5, pp. 255-304, 275-278. ③ Ifat Maoz, Andrew Ward, Michael Katz, and Lee Ross, “Reactive Devaluation of an ‘Israeli’ vs. ‘Palestinian’ Peace Proposal,”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 4 (August 2002), pp. 515-546. ④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343-355. ⑤ Deborah W. Larson, Anatomy of Mistrust: US-Soviet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⑥ W. Murray and A. R. Millett, A War To Be Won: Figh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8 · 2014 年第 2 期 国的军事能力。① 1814 年拿破仑战败以后,主要的欧洲势力始终高估了法国的力 量,尽管在那时候法兰西已经开始了长时间的相对衰落,而普鲁士的阴云却渐渐 笼罩在欧洲大陆上空。② 当然,也存在一些例外。有两个原因可能导致我们低估他国的能力,进而低 估其决心。在某些案例中,双方之间能力太过悬殊以至于优势方很容易就变得过 于自信。比如说朝鲜战争中的道格拉斯 • 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越南战 争中的美国以及 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这些案例都是一种对他国能力(进而决 心)的目中无人式的低估。在另一些例子里,那些低估对手能力(进而决心)者 是一些“突变体”(Mutants):他们的自负(和野心)驱使他们低估别人的能力并 且确信他们将取得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换句话说,许多误判都是由偏见所导致 的。③ 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以及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就属于第二类的案例。正如杰 弗里 • 布莱恩(Geoffrey Blaine)④ 在很久以前就指出的,不管出于哪种原因,领 导者对于对手能力(进而决心)的低估常常导致了战争。当然,这两种原因并不 互相排斥,当它们同时存在时,它们能彼此增强。 相对的,我们倾向于低估他国在合作中提供帮助的能力(和决心) ,这一点与 我们和他国之间的相对权力分配无关。在两个盟国之间,双方都倾向于怀疑另一 方是否能够做出那么多贡献,并且担心那些困难较多且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将由自 己来完成。当双方能力相差不大时这一偏见尤其严重 :每一方都担心另一方想“搭 便车” 。 正如前文所述,对于他国决心的不确定性通常只有当我们和他国已处于冲突 或者合作情境中时才显得重要。与在冲突情境中感知他国能力的逻辑相类似,当 对手的能力与我们基本一样或大于我们时,我们通常不会在冲突中低估对手的决 心,即使另一方在上次冲突中做出过让步。 ⑤ 所以,尽管苏联在两个超级大国间发 ① Christopher Layne,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Use of History: Neville Chamberlain’s Grand Strategy Revisited,”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3 (July 2008), pp. 397-437; Norrin M. Ripsman and Jack S. Levy, “The Preventive War that Never Happened: Britain, France, and the Rise of Germany in the 1930s,” Security Studies, Vol. 16, No. 1 (January / March 2007), pp. 32-67. ②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Clare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xx-xxxiii. ③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97-100;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④ Geoffrey Blaine, Causes of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8. ⑤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aryl Press, Calculating Credibil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Shiping Tang, “Reputation, Cult of Reputation,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1 (January / March 2005), pp. 34-62. · 19 ·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 生的大多数危机中都做出过让步,冷战期间的美国却从来没低估过苏联在僵持中 坚守立场的决心。① 相对的,当对手的能力大大低于我们自身时,我们很有可能会低估对方的决心。 麦克阿瑟低估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心,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同 他那装备精良的军队作战的可能。相似的,以色列排除了埃及会在 1973 年发动攻击 的可能性,因为它坚信埃及只会在能够攻击到以色列机场的情形下发起攻势。② 正 如勒博和贾尼斯 • 斯坦(Janice Gross Stein)③ 慧眼所识,这解释了为什么那些信奉理 性威慑理论的(粗糙)逻辑的领导者会倾向于低估对方发起挑战的决心。 寻求合作时,对他方决心(即兑现其合作承诺的决意)的不确定性会在真正 达成合作的协议之前起作用。而就如詹姆斯 • 费伦(James D. Fearon)④ 所言,这 种对他方遵守契约承诺之决心的怀疑是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障碍。在联盟内部,每 一方都担忧在对手的压力或引诱下另一方会抛弃联盟, ⑤ 尽管在现实的世界政治 中,以强制方式楔入联盟的战略是极少成功的,甚至就连选择性调和(Selective Accommodation)类的楔入战略也面临着重重困难。⑥ 如果已经处于一定程度的冲突关系中,我们在感知到潜在的不友好或敌意信 号时会倾向于轻视他方做出该项举动时所处环境的重要性。换言之,当他国的行 为不令我们称心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弱化他们面临的外部约束,即认为他们的不 善举动都缘于他们天性本恶。更重要的是,我们几乎从不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 即正是我们自己导致了他们的多疑,因而他们现在只是在对我们先前的不友好举 动做出回应。对这种可能性的忽视正是国家通常难以解开螺旋上升的安全困境这 ① Ted Hopf, Peripheral Visions: Deterrence Theor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Third World, 1965-199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② Janice Gross Stein, “Calculation, Miscalculation, and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the View from Cairo,” in Robert Jervis,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isty Press, 1985, pp. 34-35; Janice Gross Stein, “Calculation, Miscalculation, and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the View from Jerusalem,” in Robert Jervis,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eds.,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pp. 60-88. ③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p. 325-328. ④ James D. Fearon, “Bargaining, Enforce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2 (Spring 1998), pp. 269-305. ⑤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July 1984), pp. 461-495; 同样也可以在以下文献中找到相关证据,Yoichi Funabashi, Alliance Adrift,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9。 ⑥ Timothy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Spring 2011), pp. 155-189. · 20 · 2014 年第 2 期 种恶性动态的重要原因。① 相反,当感知来自其他国家的潜在的友好信号时,我们倾向于夸大导致其做 出该种举动的外部约束。另一方做出让步是因为在既定的外部环境中他别无选择。 换言之,当他国行为令我们满意时,我们倾向于强调他国所面临的外部约束。而 如果我们能够将这种外部约束归因于我们自身的压力,情况就更是如此了——他 们的行为符合我们的心意是因为我们迫使他们这么做——赫鲁晓夫执政后,苏联 在冷战阶段至少部分地受这种动态所推动。尽管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存在, 赫鲁晓夫可能真的希望与美国及其盟友“和平共存” 。 ② 但是,美国的核心决策者 并不准备相信。 实际上,上文中提到的这些偏见和误差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在解释他方行 为时我们常常陷入其中,哪怕拥有足够的后见之明也依然如此。当他国行为合我 们之意时,我们会将导致行为的主要原因归因于我们自己(作为外部原因) ,而 几乎没有给予那些导致对方行为的内生动力以肯定。当他国行为不合心意时(同 样从我们的视角来看) ,我们就会将主要原因归因于他方的恶意和精明算计(作 为内部原因)。因此,毕胜戈(Richard Bitzinger) ③ 和威廉 • 沃尔福思(William Wohlforth)④ 都坚持认为戈尔巴乔夫只是迫于压力才屈服于西方的,他自身观念的 成分在其决定的形成中不起主要作用。⑤ 在评估他国的威胁和保证信号的可信度时,冲突情境和合作情境之间的差别 ①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rles L. Glas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2 (July 1992), pp. 497-538;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Chap. 2. ② Melvi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Deborah W. Larson, Anatomy of Mistrust; Andrew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 3. ③ Richard Bitzinger, “Gorbachev and GRIT: Did Arms Control Succeed Because of Unilateral Actions or in Spite of Them?,”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15, No. 1 (April 1994), pp. 68-79. ④ William Wohlforth,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 2 (Winter 1994/1995), pp. 91-129. ⑤ 对于这些文献的批判,参见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p. 369-376. 在此笔者需要指出的是,在解释行为和解释结果之间存在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在 我们看来结果是积极的(或令人满意的),我们通常更多地将其归因于我们自己的行动而很少归因于 他人的行动,而当结果消极(或不令人满意)之时我们的做法则相反。因此,由于冷战以有利于美国 的方式结束,美方的评论者大多用美国的行为来解释这一结果,参见William Wohlforth,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 2 (Winter 1994/1995)。相对的,当涉及所谓 的在东南亚美国相对于中国的影响力的下降时,许多评论者将其主要归因于中国的“魅力攻势”和可 能隐藏其后的邪恶构想,参见Josh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Robert Sutter, “China’s Rise: Implications for U.S. Leadership in Asia,” Policy Studies, Vol. 21, Washington: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2006。 · 21 ·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 会变得尤其明显。根据关于冲突中(特别是威慑和强制中)有成本信号传递的研 究成果,一个国家威慑的可信度是关于一国(军事)能力、利益、决心和情境约 束的函数(所有变量均为国内观察者感知到的情况)。① 更形式化的表达为,一国 在其对手思维中的威胁可信度 CT 可由以下等式来决定 : 一国军事能力 × 利益 × 决心 C T = f( ) 国家面临的能被其对手感知到的情境约束 根据关于寻求合作的有成本信号传递的研究成果,一个合作行为,即一个战 略示善姿态(Reassurance Gesture)② 的可信度是一个关于其成本、风险(即在姿 态没有得到相应回报时将产生的潜在损失) 、潜在收益(比如说,不论另一方是否 正面回应都将节省下的资源加上另一方正面回应时获得的其他好处)以及信号发 送者面临的情境约束(即情境需要在多大程度上驱动着保证信号的传递) ,同样所 有变量均为接收者感知到的情况。更为形式化的表达为,保证信号的可信度 CA 可 由以下等式来决定 : 从这两个结构截然不同的等式来看,很显然我们倾向于高估他国威胁信号的 可信度(因为分子中的各项是相乘的), 除非在构成其威胁信号的各部分(即能力、 利益和决心)中至少有一个值变得极端小。相对的,我们倾向于低估他国保证信 号的可信度(因为分子中的各项是相加或者相减的) 。在实践中,我们低估他国保 证信号的可信度的倾向更为严重,因为我们倾向于低估另一方可能承受的成本和 风险而夸大其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相对的,我们高估他国威胁信号可信度的倾 向也更为严重,因为我们总是将另一方威胁信号背后的情境约束最小化。 合作情境下归因与冲突情境下归因之间产生这种对比的支撑基础是“为生 存而恐惧”的心理。这一心理产生了诸多的偏差,其中的部分已经被贴上了诸如 “敌意归因误差”(Hostile Attribution Error) 、“险恶归因偏差” (Sinister Attribution ① 在冲突性情境中,另一方已经被假定为是恶意的。换句话说,我们把另一方将采取对我们不利 的行动的可能性估计为1。 ② 在翻译此文时,英文版中“reassurance”一词没有特别好的直译。经过仔细考虑,笔者将 “reassurance”翻译成“示善”。详细的讨论见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Chap. 5。 · 22 · 2014 年第 2 期 Bias)或“迫害认知” (Paranoid Cognition)之类的标签。① 这一系列的动态强化并 维系了我们对潜在危险的警觉,并且保护我们不会轻易陷入松懈。在为了(个人 或群体)生存的世界里,“有备无患,未雨绸缪”是一句至理名言。② 需要牢记的一个关键点是,在心理动态为冲突与合作增加了一类内生动态的 同时,冲突和合作也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知觉。正如冷战所生动诠释的那样,③ 随 着对抗的延长,对抗双方都越来越认为对方是不可救药的侵略成性,并且从根本 上认定对方的目标是非法的,意图是恶意的,从而渐渐回到只关注能力和决心的 更为简单的认知方式(即心理简化) 。④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双方变得对彼此的目 标和意图毫无兴趣,眼中只剩下能力和决心。只有当冲突性情境结束之后(虽然 依然伴随着一些挥之不去的仇恨) ,国家才会缓慢地开始意识到彼此都并非天生侵 略成性,继而再次对彼此的目标和意图产生兴趣。 四 人们通常无法正确认知事物的证据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将提供一些表明我们通常无法正确认知不确定性的各个维 度的证据。当然,这绝不是说笔者能正确认知所有事物,并且能将所有错误认知 加以矫正。首先,提供一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文献中的证据,说明许多国际关系 理论学者未能正确认知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其次,提供一些来自现实世界政治 的证据,这些证据目前大部分来源于二手文献资料。 (一)无法正确认知挑战 :国际关系研究文献中的证据 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自我中心主义地)相信其对事物的认知比政策制 定者更为正确,然而事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国际关系学者们会犯的错误可以归 ① Kenneth A. Dodge, Gregory S. Pettit, Cynthia L. McClaskey, and Melissa M. Brown, Social Competence in Children, pp. 1-85; Kenneth A. Dodge and Daniel R. Somberg, “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es among Aggressive Boys Are Exacerbated under Conditions of Threats to the Self,” Child Development, Vol. 58, No.1 (February 1987), pp. 213-224; R. M. Kramer, “ Paranoid Cognition in Social Systems: Thinking and Acting in the Shadow of Doubt,”Perception and Phenomenal Causa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2, No. 4 ( November 1998), pp. 251-275; R. M. Kramer and D. M. Messick, “Getting by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Our Enemies,” in C. Sedikides, J. Schopler and C. A. Insko, eds., Intergroup Cognition and Intergroup Behavior,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8, pp. 233-255. ② 关于这方面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Fear (and Trust): Or why i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ifficult?” paper presented in the 49th Annual Con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n San Francisco, March 26-29, 2008。 ③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chap. 12; Sergei Zubov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④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64-65; Shiping Tang, “Reputation, Cult of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1 (January / March 2005), pp. 50-54. · 23 ·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 为三大类,与上文所述的多维度造成的认知挑战的三个层次基本一致。 1.将各维度混为一谈或以不一致的方式来使用这些维度 国际关系学者最明显的错误或许在于他们在许多讨论中未能将五个维度区分 开来,并且没有以一致的方式来使用这些维度。① 例如,兰德尔 • 施韦勒(Randall L. Schewller)② 认为动机与意图可以互换, 即使亚瑟 • 内维尔 • 并指出“‘意图’这一概念通常指行为体的计划与目标” 。③ 同样, 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确 实对希特勒的野心没什么把握,但安德鲁 • 巴罗斯(Andrew Barros)和塔尔博特 • 伊姆莱(Talbot C. Imlay)④ 等人却断言张伯伦对希特勒的“意图”茫然无知。这 些学者们混淆了意图与目标(或者说野心) 。 最近, 笔者在尝试整理归纳不确定性的各种概念时,发现布赖恩 • 拉斯本(Brian C. Rathbun)正确地指出,不确定性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而言意味着“国家对互 动者的意图、利益与权力信息的缺乏”。⑤然而,在讨论国际关系中理性选择路径 (Paul K. Macdonald)一样, 的不确定性研究时,⑥ 拉斯本同他之前的保罗 • 麦克唐纳 没能够认识到理性选择路径最感兴趣的是能力和决心的不确定性,同时它将意图 固定为恶意,进而将意图的不确定性边缘化,甚至在假定中予以排除。⑦ 这一点在 费伦的作品中是再明显不过的了。⑧ 另一些学者尽管区分了意图与动机 , 却并未以一致的方式来使用这两个概念。 例如埃文 • 蒙哥马利(Evan Braden Montgomery)声称要使用“动机”与“偏好”来 ① 对战争与和平博弈模型存在的问题的详细论述见第五部分。 ②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8. ③ 参见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 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Spring 1996), pp. 103-104; Andrew Kydd, “Sheep in Sheep’s Clothing: Why Security Seekers Do Not Fight Each Other,” Security Studies, Vol. 7, No. 1 (Fall 1997), pp. 126, 152。 ④ Andrew Barros and Talbot C. Imlay, “Correspondence: Debating British Decision Making toward Nazi Germany in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1 (Summer 2009), p. 276. ⑤ Brian C. Rathbun, “Uncertain About Uncertainty: Understanding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a Crucial Concep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4 (December 2007), pp. 537, 541-545. ⑥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Summer 1995), pp. 379-414. ⑦ Paul K. MacDonald, “The Virtue of Ambiguity: A Critique of the Information Turn in IR theor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olumbia University, 2002, pp. 5-7. ⑧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Summer 1995), p. 381. · 24 · 2014 年第 2 期 表示国家对目标的偏好,而用“意图”来表示国家对战略的偏好。① 然而,蒙哥马利 对于这些概念的利用并非总是前后一致的。他时常论及“一国可以显示其善意动机 的首要方法”和“一个善意国家试图证明其动机”、 “显示其善意动机”、 “对他国动 机的不确定并且恐惧他国会利用所有让步来牟利”以及“显示他们动机”等。② 在所 有类似的情形中,动机均应该被“意图”所替代。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查尔斯 • 格拉泽(Charles L. Glaser)在抱怨杰维斯③ 对螺 旋模型和威慑模型的阐释仅仅关注了国家的意图而相对忽视了国家的扩张动机, 他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对国家的意图与动机予以同等的关注。④ 格拉泽由此引入了 一个他自称更为精致的从两个维度区分国家动机的方法。通过结合这两个动机维 度,即“贪婪的”与“非贪婪的” (Greedy Versus Not Greedy)、 “永远安全的”与“不 ,格拉泽声称国家可以被分为四种类型, 安全的”(Always-Secure Versus Insecure) 因而他的理论增强了螺旋模型与威慑模型的解释力,并为国家军事战略归纳出了 更为精细的对策。格拉泽的“永远安全的”与“不安全的”二分法显然是无效的, 因为根据他自己所信奉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所有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都是不 安全的。更糟糕的是,格拉泽提出的框架中的第一维度取决于一国是否对不以安 全为目标的扩张感兴趣——感兴趣的是贪婪的国家,反之则不是。由此,贪婪与 非贪婪的二元论并非关乎动机(这里可被理解为目标) ,而是本质上再次提领了意 图维度,因而不过是增加了两个新的标签,没有带来什么实质的益处。 此外,格拉泽总是将“善意的”与“恶意的”置于动机与目标之前。 ⑤ 然而, 根据他所信奉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对目标的偏好是由国际政治的无政府 属性所决定的。⑥ 换句话说,结构现实主义假定国家的目标偏好是固定的,所有的 国家将安全视为最低限度的需求。⑦ 由于权力仍然是安全的重要支柱,并且权力与 ① Evan Braden Montgomery, “Breaking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Realism, Reassurance, and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2 (Fall 2006), p. 153, footnote 9. ② Evan Braden Montgomery, “Breaking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Realism, Reassurance, and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2 (Fall 2006), pp.158,160,162. ③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④ Charles L. Glas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2 (July 1992), pp. 499-508. ⑤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 60, 67-68, 70. ⑥ Robert Powell,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Neorealist-Neoliberal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Spring 1994), pp. 313-344。亦可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ion-Wesley, 1979。 ⑦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9. · 25 ·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 安全相互作用,追求权力与追求安全之间不可能存在明显的界限。① 所以,追求权 力不必然意味着恶意,追求安全也不必然意味着善意。因此,对于结构现实主义 而言,国家的动机或目标在规范意义上是中性的,只有意图或者对战略的偏好可 以被视为恶意或善意。因而,只有放在意图前的形容词才能够被用来区分和标示 国家所属的两种基本类型,即恶意国家与善意国家。鉴于存在上述缺陷,格拉泽 给安全困境和螺旋模型的扩展带来的是更多的困惑,而不是更精细的解释力。② 2.非系统与非动态的理解 由于不确定性的五个维度组成了一个动态系统,我们需要一种系统的、动态 的路径来理解它们。③ 不幸的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通常以非系统与非动态的路径 来理解不确定性。这种非系统与非动态的路径是无用且易于误导的,其大大削弱 了五个维度变化所拥有的解释力。 针对不确定性的非系统性思维的一种表现是单独拿出一个或两个维度作为自 变量并忽视了其他维度。安妮 • 萨托利(Anne Sartori)推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 朝鲜战争发生之前中国大陆攻打台湾之誓言的无法兑现(即“中国的虚张声势” ) 使中国“威胁”干预朝鲜战争的可信度被大幅削弱。就因为这个缘故,美国主要 的决策者们不会认为中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威胁”是可信的。④ 萨托利由此排除了 多数美国决策者因低估中国的作战能力而不把中国的“威胁”放在心上的可能性。 然而,即使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虚张声势在一定程度上诱使美国忽略了中国的警告, 但一个可能更为合理的解释是美国决策者对中国作战能力的低估是导致其不认真 “只有当有足够的权力支撑并且为 对待中国“威胁”的更为关键的原因。⑤ 毕竟, 清晰的目标服务时,威胁才是可信的”。⑥ 不确定性的非动态研究路径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我们通常倾向于认为一旦我们 为某一国家贴上了某种特定类型的标签,那么标签就不应该被摘下,不论之后发 生了什么。因此,格拉泽坚持认为一个机会扩张主义国家(即一个至少在某段时 间内是恶意的国家)只要其扩张是受安全所驱动就仍然是一个追求安全的国家(或 ①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 42. ② 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Chaps. 1 and 2。 ③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④ Anne Sartori, “The Might of the Pen: A Reputation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1 (Winter 2002), pp. 137-140. ⑤ 萨托利并未发现直接的证据将美国的决策者们对朝鲜的看法与对台湾地区的看法联系起来。 ⑥ Daryl Press, Calculating Credibility, p. 143. · 26 · 2014 年第 2 期 者更精确地说,一个善意国家)。 ① 然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在无政府状态中所有 国家都追求安全。因循着同样的逻辑,许多学者都试图将某种情境认定为安全困 境并假定这种情境将持续存在。但在现实世界中,这种情境却能够从安全困境转 变为螺旋,再从螺旋转变回安全困境。所以,这些学者就倾向于追问冲突是否是 由安全困境所导致的,而不是去追问冲突是否已经从安全困境转变为了螺旋,并 进而转变为战争。 ② 在以上这两种情形中,一国(或一种情境)在不同类型间来 回转变的可能性都遭到了忽视。许多理论学者似乎忘记了标签仅仅是一种启发式 工具,它们并非一旦贴上就永无揭下之日,因为五个维度本身是都可变的。这也 就是说,国家的类型(或身份)是可能发生变化的,这一观点在建构主义流行的 很久以前 ③ 便被人所提及。④ 因为假定一国的标签是一成不变的,一些现实主义 的理论家把国家行为的现实主义理论变成了静态的理论。这完全是多此一举。 非系统和非动态思维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也包括政治家)的一个最突出 的后果是我们倾向于强调意图只可能从善意迅速变为恶意,却不会从恶意迅速变 为善意。⑤ 换句话说,我们很容易相信他国从善意变为恶意,可是当该国的意图已 经从恶意转变为善意时,我们却十分抗拒于改变对该国的印象。然而,从逻辑上看, 如果一个国家能迅速地从善意转变为恶意(比如说由于领导人的变化) ,我们就没 有任何理由认为一个国家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和速度从恶意转变为善意。冷战的历 史提供了充分的例证说明领导人的变化可以有效地改变一国的性质,比如戈尔巴 乔夫时期的苏联同斯大林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就大不相同。 ⑥ 冷战后,我们确 定地认为在布什和新保守主义掌权后美国已经成为了恶意的国家,而如今,奥巴 马已经使美国重回善意国家的阵营。 3.未能把握冲突与合作情境所带来的不同挑战 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未能认识到,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在我们与 ① Charles L. Glas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2 (July 1992), pp. 497-538; Charles L. 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 (October 1997), pp. 171-201. ②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Chaps. 2 and 3. ③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45-84. ④ 也可参见Robert Jervis and Thierry Balzacq, “The Logic of Mind: Interview with Robert Jerv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3 (July 2004), pp. 559-563。 ⑤ 这是一个基于恐惧心理而产生的一种即时预测,我们的认知严重地向不安全或恐惧倾斜, 而远离安全、满足与信任。对这方面的更为详尽的讨论,参见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Fear (and Trust): Or Why i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ifficult?” paper presented in the 49th Annual Con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n San Francisco, March 26-29, 2008。 ⑥ Deborah W. Larson, Anatomy of Mistrust; Melvin P.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the Mankind: U.S.,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7;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appendix I. · 27 ·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 他国身处情境不同(如冲突、合作或模棱两可)时对我们的认知造成的挑战可能 也是不同的。实际上,许多既有研究都明示或暗示了不确定性的不同维度在各种 情境中没什么区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道格拉斯 • 吉布勒(Douglas Gibler)假定“违反防御条约与违反互不侵犯或中立条约将产生同样的不诚实的声 誉” 。 ① 然而,违反互不侵犯条约或中立条约比违反防御条约要糟糕得多,后者不 过是传达出合作伙伴的迟疑不决,但前者则意味着(所谓的)伙伴或朋友实际上 是恶意国家。事实上,吉布勒接下来就写道 : “违反中立条约或互不侵犯条约相比 忽视防御条约往往制造了对条约的更为露骨的亵渎,因为这类违反常常由一国攻 击其盟友所引起。 ”不过,他之后仍然在各种论述中坚持将它们视为相同的。 相似的,格雷戈里 • 米勒(Gregory Miller)② 致力于研究商业联盟(作为合作 的一种形式)中以责任为荣的决心所带来的声誉,以此来挑战戴维 • 默瑟(David Mercer)关于由决心所带来的声誉也许在冲突中并不显得那么重要的论点。③ 很明 显,米勒相信,对合作(例如商业联盟)中声誉的领悟可以直接移植到(国际) 冲突中的声誉上。 (二)误判事实 :来自现实世界的证据 从事后来看,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政治家们在理解他国行为时经常会出错。 鉴于众多学者已广泛而深入地就此项议题进行了研究,④ 笔者在这里只是强调一些 关键的方面,特别是突出冲突情境中知觉与合作情境中知觉的比较。 政治家们总是高估他国的恶意,特别是在冲突的情境中。这种情况发生之普 遍使杰克 • 利维(Jack Levy)断言这些对恶意的高估构成了“错误知觉最为普遍的 形式”。⑤ 冷战期间,美国政策的决策者们(如乔治 • 凯南、保罗 • 尼采、哈里 • 杜 鲁门等)强烈相信苏联真的热衷于毁灭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因而认为,朝鲜 ① Douglas M. Gibler, “The Costs of Reneging: Reputation and Alliance Form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No. 3 (June 2008), p. 437. ② Gregory, D. Miller, “Hypotheses on Reputation: Alliance Choices and the Shadow of the Past,”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3 (Spring 2003), pp. 40-78. ③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④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Jack S. Levy, “Misperceptions and the Causes of War: Theoretical Linkages and Analytical Problem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1 (October 1983), pp. 76-99; Janice Gross Stein, “Building Politics into Psychology: The Misperception of Threat,”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9, No. 2 (June 1988), pp. 245271;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aryl Press, Calculating Credibility. ⑤ Jack S. Levy, “Misperceptions and the Causes of War: Theoretical Linkages and Analytical Problem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1 (October 1983), p. 88. · 28 · 2014 年第 2 期 战争(越南战争也是一样)是苏联设计的一场对美国决心的测试,是一场由共产 主义而非民族主义驱动的战争。① 在另一边,苏联领导人同样夸大了美国摧毁苏联 的险恶用心,② 所以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冷战史的大部分都是由不断升级的军备竞 赛、代理人战争以及与促成合作之良机痛失交臂所构成的悲哀故事。③ 在试图理解埃及总统迦玛尔 • 阿卜杜尔 • 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这一举 动背后的深意时,英国首相安东尼 • 艾登(Anthony Eden)将纳赛尔视为另一个 希特勒式的独裁者,而不是一位需要打动国内与区域内的广泛听众的“泛阿拉伯 民族主义者”。对纳赛尔的这一印象的固化使艾登不可能去考虑对纳赛尔让步的 可能性。④ 在双方能力大致相等的情况下 , 政治家们同样倾向于高估对手的能力和决心。 在 1936-1938 年的关键时期,英国和法国本可以对纳粹德国发动一场防御性战争, 但两国始终高估了德国的力量与决心。⑤ 结果是,在希特勒最为脆弱和迟疑不决的 时候,英法两国却拒绝与之针锋相对。⑥ 冷战的早期为我们呈现了另一个经典案例。在对 1957-1961 年期间的“导弹 鸿沟” (Missile Gap)传奇进行考察时,乔纳森 • 罗逊(Jonathan Renshon)指出, 美国领导人始终高估苏联的能力,“将他们的对手(想象成)比实际更强大、更具 有进攻性、也更危险的敌人” 。⑦ 保罗 • 尼采(Paul H. Nitze)在起草 NSC-68 文件时,同样高估了苏联日益增 长的绝对能力而将美国的能力视为稳定不变的。他因此也高估了苏联的相对能力, 而实际上即使将早年苏联制造原子弹和中国革命的成功计算在内,对美苏间相对 实力的更为乐观的评价仍应成立。两个超级大国同样高估了彼此挑战另一方的决 ①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5, Chap. 4; Melvi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② Sergei Zubov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③ Deborah W. Larson, Anatomy of Mistrust; Melvin P.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the Mankind. ④ Janice Gross Stein, “Building Politics into Psychology: The Misperception of Threa,”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9, No. 2 (June 1988), p. 249. ⑤ 然而,英法两国均低估了希特勒的野心。这或许是一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而产生 的动机偏见。由于这些记忆,直到1936年,英法两国的决策者们才确信了希特勒的邪恶意图。关 于这方面更为详细的论述,参见Christopher Layne,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Use of History: Neville Chamberlain’s Grand Strategy Revisited,”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3 (July 2008)。 ⑥ Norrin M. Ripsman and Jack S. Levy, “The Preventive War that Never Happened: Britain, France, and the Rise of Germany in the 1930s,” Security Studies, Vol. 16, No. 1 (January / March 2007), pp. 48–58. 同样 也可参见下文的讨论。 ⑦ Jonathan Renshon, “Assessing Capabilit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iased Overestimation and the Case of the Imaginary ‘Missile Gap’,”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2, No. 1 (February 2009), p. 116. · 29 ·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 心,并且同时害怕在让步或妥协后会失去关于自己决心的声誉。① 由于族群中心主义(或者更为确切地说,缺乏移情能力),政治家们通常认为, 一国对其他国家的恐惧是合情合理的,但其他国家对该国的恐惧则是不合情理的。 因此,迪安 • 艾奇逊(Dean Acheson)认为苏联没有恐惧北约的理由,而美国及其 盟国却有理由恐惧苏联。同样,当美军朝鸭绿江推进时,中国应该没什么好怕的, 约翰 • 肯尼迪(John F. 而美国对苏联的扩张主义的恐惧则是理所应当的。② 类似的, Kennedy)认为猪湾入侵事件不过是一场颠覆诡计,但尼基塔 • 谢尔盖耶维奇 • 赫 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在古巴部署导弹却是具有挑衅与侵略性质 的行为,而赫鲁晓夫对于这些情境的解读则恰恰相反。③ 与上述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家们倾向于低估盟友们为集体福利做出贡 献的能力、利益以及决心。因此,自从尼克松访问中国而未知会日本(即“尼克 松冲击”)之后,日本就一直怀有被美国“遗弃”的恐惧。许多日本政治家开始怀 疑美国对美日联盟做出的承诺,并害怕在时机成熟之后美国会为了中国或其他亚 洲国家而抛弃日本。④ 联盟政治的整个被抛弃之恐惧的动态都能反映出低估盟友贡 献联盟的能力、利益和决心这一机理的影响。⑤ 此外,处于正在发展的合作关系之中的双方几乎总是倾向于相信另一方选择 合作是不得不为之,并且多半是由于我们不懈地施压所致。 ⑥ 因此,当印度和中 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开始走向和解时,双方都相信另一方选择合作 本质上是迫于外部的压力。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压力是 1989 年后的外交孤立状 态 ;对于印度而言,则是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双方都弱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 自 1962 年中印两国边境冲突之后,两个国家内部都持续地存在着对两国和解的 呼吁。⑦ 同理,美国的主要决策者都曾经很不乐意承认苏联之所以选择与西方合 作,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确实与以往大不相同。⑧ 冷战初期的那几年(1945-1950 年)很好地佐证了以决心和能力为基础的计 ①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aryl Press, Calculating Credibility; Shiping Tang, “Reputation, Cult of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1 (January/ March 2005), pp. 34-62. ②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67-74. ③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p. 309-314. ④ Yoichi Funabashi, Alliance Adrift. ⑤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July 1984). ⑥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343-349. ⑦ Jing-dong Yuan and Waheguru Pal Singh Sidhu, China and India: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3. ⑧ Deborah W. Larson, Anatomy of Mistrust; Andrew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 8. · 30 · 2014 年第 2 期 划系统逐渐形成的过程。从乔治 • 凯南主导的 NCS-20/4 文件到保罗 • 尼采主导的 NSC-68 文件,① 美国对苏联的知觉越来越集中于能力与决心维度,将苏联的利益 固化为不可救药的野心勃勃,② 而将苏联的意图固化为不可救药的侵略成性。外部 约束力同样被视而不见,在美国人眼里,“克里姆林宫能够选择任何可以利用的有 效手段来执行它的基本设计” 。③ 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思考则如同美国的一个镜像。④ 五 误判事实的后果 由于我们对不确定性维度的误判的整体政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本文将重点 聚焦于误判事实在理论上会产生的后果。笔者的研究表明,无法正确认知不确定 性维度已然给我们对国际关系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的理解制造了可怕的陷阱。有 时,我们的讨论已经彻底失去了连贯性和一致性。 (一)区别在于“概率性”与“可能性”? 区分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或者其他非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一 个非常有影响的构想是斯蒂芬 • 布鲁克斯(Stephen G. Brooks)的“概率性与可能 性之分” (Probability versus Possibility) 。⑤ 根据布鲁克斯的观点,进攻性现实主义 (或者更精确地说,在布鲁克斯的作品里是指结构现实主义)是一个由“可能性” (Possibility)驱动的理论,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则是由“概率性”(Probability)驱 动的理论。不幸的是,布鲁克斯在讨论“概率性”和“可能性”问题时没有明确 区分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因而他没有认识到,在估计另一国家的能力、利益、 决心和外部环境方面,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是一个“概率性”的理论。只有在估计 意图时,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一个“可能性”理论。⑥ 由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既是 “可能性”的也是“概率性”的,而非仅仅是“可能性”的。⑦ ①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 Chaps. 2-4. ② 本文英文版此处缺了两个单词。原文应该是“while fixing Soviet Union’s interests as incurably ambitious and intentions as incurably aggressive”。中文版是根据正确的英文翻译的。 ③ S. Nelson Drew, ed.,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with analyses by Paul H. Nitze,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93, p. 44. ④ Sergei Zubov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⑤ Stephen G. Brooks,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3 (Summer 1997), pp. 445-477. ⑥ Shiping Tang, “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3 (September 2008). ⑦ 由于多数现实主义理论假定国家是战略的或者“理性的”的行为体,又由于许多人又将“理性 的”理解为根据“概率性”来行动并且“可能性”是一种“概率性”的极端表现,布鲁克斯的公式对许 多人来说都有些极端。在这里我感谢安迪•基德(Andy Kydd)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 31 ·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 沿袭布鲁克斯的构想,杰弗里 • 托利弗(Jeffery W. Taliaferro)① 赞扬戴尔 • 卡 普兰(Dale Copeland)② 解决了评估他人行为时的“概率性 / 可能性之分”问题(由 此整合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现实主义) ,并将卡普兰的理论归入防御性现实主义。托 利弗对卡普兰的推崇和他对进攻性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区别的误解同样也是因为没 有把握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 虽然卡普兰③ 开始时将他国现在和未来意图的不确定性视为其理论中一个重 要的驱动因子,并且似乎同意将意图的不确定性置于其理论的中心位置,但他最 后的总结却是 :一个国家是否会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既取决于其感知到的相对衰 落之性质(如衰落的速度、深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也取决于在特 定的系统权力分配(即“极性”)条件下这场预防性战争是否会取得胜利。国家对 预防性战争的算计成为了纯粹的成本-利益计算(虽然要更为复杂一些) ,其中涉 及了能力、决心、利益和外部约束,而对意图的不确定性则在任何时候都未在其 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尽管卡普兰的预防性战争理论是由“概率性”所驱动的, 但其却是典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这是因为是否将他者的意图假定为最恶是 划分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其他所有非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真正的界线 :进攻性现 实主义是,而所有非进攻性现实主义都不是。 ④ 如此一来,托利弗对卡普兰解决评 估他人行为时的“概率性与可能性之分”问题的赞美是有名无实的,并且他对进 攻性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区别的理解是具有误导性的。⑤ (二)意图的妄想与结构进攻性现实主义 意图的不确定性毫无疑问应该被置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位置。 ⑥ 然而一 些国际关系学者也许在这方面走过了头——他们过于强调了意图的不确定性而 ① Jeffer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2000-2001). ② Dale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③ Dale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p. 4. ④ Shiping Tang, “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3 (September 2008). ⑤ Shiping Tang, “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3 (September 2008);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Chaps 1 and 6. ⑥ Stephen Walt, The Origin of Alliance; Charles L. Glas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2 (July 1992), pp. 497-538;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Andrew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an C. Rathbun, “Uncertain About Uncertainty: Understanding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a Crucial Concep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4 (December 2007), pp. 533-557; Shiping Tang, “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3 (September 2008); 也可参见Bertram F. Malle, How the Mind Explains Behavior: Folk Explanations, Meaning, and Social Interaction。 · 32 · 2014 年第 2 期 边缘化了其他维度。更关键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对于意图的理解是固定而静 态的,而且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既然国家能够迅速从善意转变为恶意,那 么也能够以同样的速度从恶意转变为善意。而在他们看来,既然意图能从善意 转变为恶意却无法再转变回来,那么将他国意图假定为最恶就不失为一种更好 的做法。结果就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成了他们选择的路径。对他者未来(恶意) 意图的过分强调以及继而所做出的假定意图最恶是逻辑或理性之选择的断言, 是约翰 • 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 ① 和卡普兰 ② 所拥护的结构进攻性 现实主义的一个默而不宣却无法绕开的基石性假定——其正是进攻性现实主义 的“第六元素”。并且,正是这种对他人意图的最恶假定,而不是其他诸如如何 划分所得和传递善意信号之类的原因,使得进攻性现实主义否定了在无政府状 态下除面临共同威胁时组成临时联盟之外还存在合作的可能性。 ③ 然而,这一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础是有问题的,它没有认识到,意图在通常 情况下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发生变化(从善意变为恶意或者相反) 。意图的变化多半 与一国的领导层、能力及目标的变化有关。这就为其他行为者提供了评估对方意 图的时间。最重要的是, 即使一国的意图从善意转变为恶意, 也只有当其(进攻性) 军事能力发生实质性变化之后其才能够造成真正的威胁。尽管希特勒也许很久以 前就是个有谋杀倾向的精神病患者,但大致到 1936-1938 年左右希特勒德国才成为 一个严重的威胁。④ 这一延迟给了其他国家机会来观察对方的行为(包括其军事能 力和姿态) 、评估其意图并进而据此设计针对该国的政策。⑤ 当这些方法成为可能 时,将他国意图假定为最恶(并且固定对他国意图的印象)就不会永远是最好的 下注手段。最关键的是,从对他国意图的不确定到将他国意图假定为最恶之间存 在一个逻辑跳跃。为了给进攻性现实主义一个更坚实的基础,进攻性现实主义者 们需要为他们的理论寻找一个更好的锚点。 (三)从不完全信息到承诺问题 主要由我们无法正确认知不同维度造成的另一个后果的一个典型示例是以“不 ①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② Dale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③ Shiping Tang, “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3 (September 2008), pp. 465-466. ④ Christopher Layne,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Use of History: Neville Chamberlain’s Grand Strategy Revisited,”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3 (July 2008); Norrin M. Ripsman and Jack S. Levy, “The Preventive War that Never Happened: Britain, France, and the Rise of Germany in the 1930s,” Security Studies, Vol. 16, No. 1 (January / March 2007). ⑤ 实际上,其他国家也许可以采取一些办法来影响目标国的国内政治,使那个国家的“希特勒”无 法获得权力或维持权力,尽管这肯定不会是件容易的事情。 · 33 ·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 完全信息”为基础的战争模型。① 这些模型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假定在完全信息的条 件下,战争或冲突将不会发生。然而,显然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当一国发现另 一国从本质上是无可救药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比如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 时,该国必将选择进攻,因为投降不在其选择范围内。在族际政治中,冲突爆发 是因为一方或双方都是恶意的,并且另一方或双方都对此心知肚明,而不是因为 双方不确定彼此的意图。因此,完全信息不但未必能阻止战争,而且关于一方之 恶意的完全信息实际上可能引发一场战争。② 同样的,当一方或双方能够确定对方 坚持立场的决心时,战争也可能爆发。因为这些缺陷,基于不完全信息的战争博 弈模型“对某些持续冲突的解释是很无力的,并且其对一些案例历史的解读也相 当之匪夷所思” 。③ 毫无疑问,只有当我们将不确定性的多种维度拆解开时,我们 才能把“完全信息能消除战争”这个普遍存在于各种关于战争的“不完全信息” 研究中的古怪结论去除掉。 另一个颇具影响力但对各个维度的理解存在问题的构想是由费伦(Fearon) (Time 首 创 的“ 承 诺 问 题 ”。 ④ 莫 妮 卡 • 托 夫 特(Monica Toft) 对“ 时 间 线 ” Horizon)的强调具有同样的潜在含义 :所有五个维度都会变化是“时间线”成为 一个问题的唯一原因。⑤ “承诺问题”的概念不仅没有让问题清晰化,而且让问题更加混乱。⑥ 第一, 通过假定动机(根据费伦的解释,“承诺问题”指的是目标,贪婪或征服的欲望) 不会变化,⑦ 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就被假定掉了——无论其表述是“承诺问 题”还是动机的不确定性。当动机被假定为是固定的而意图被假定为不存在(或 者在某种程度上被永恒的“承诺问题”所取代)时,费伦一度曾试图引入的安全 ①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Summer 1995), pp. 379-414. Robert Powell, In the Shadow of Power: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Paul K. MacDonald, “The Virtue of Ambiguity: A Critique of the Information Turn in IR theor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olumbia University, 2002; Robert Powell, “War as a Commitment Probl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0, No. 2 (Winter 2006) ; Jennifer Mitzen and Randall Schweller, “Knowing the Unknown Unknowns: Misplaced Certainty and the Onset of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20, No. 2 (2011), pp. 2-35. ③ Robert Powell, “War as a Commitment Probl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0, No. 2 (Winter 2006), pp. 170, 172-176. ④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Summer 1995), pp. 379-414, esp. 401-409; 也可参见Robert Powell, “War as a Commitment Probl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0, No. 2 (Winter 2006)。 ⑤ Monica Duffy Toft, “Issue Indivisibility and Time Horizons as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1 (January / March 2006), pp. 34-69. ⑥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Summer 1995), p. 401. ⑦ 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即使动机保持不变,行为体的意图仍然可能发生变化。 · 34 · 2014 年第 2 期 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消失了,因为形成安全困境最主要依赖的一个条件正是国家 的意图可能会向最糟糕的方向转变。① 第二,费伦注意到,导致承诺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即使合作性的交易已经 达成,行为体仍然有欺骗或背叛的动机。正是这一承诺问题使得国家之间难以达 成妥协,纵然战争的代价是如此高昂。然而,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交易已经达成后, 国家还是会改变其想法(即选择欺骗)并偏向于采取一个完全不同(即对抗性) 的战略。而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第三,正如埃里克 • 加兹克(Erik Gartzke) ② 指出的,当用费伦的逻辑来推 导一个逻辑结果时,将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既然承诺问题是永恒的,那么战争 就不应该被停止。所以我们应当持续进行战争或为战争而准备,直到我们至少建 立起一个区域性帝国为止。同时,因为承诺问题是永恒的,所以得到安全的最好 的途径便是在任何有利的时机下发起预防性战争。然而,即使在非洲国家之间也 很少发动改变彼此边界的战争。费伦因此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很多根 据他的逻辑承诺问题应该是最为严重的领土争端案例中,许多妥协仍然能够达成 并为当事国所遵守。另外,国家还有其他选择,它们可以简单地冻结搁置纠纷, 使争议退回原处。 第四,通过假定国家(或领导人)是风险规避(Risk-Averse)或风险中性 (Risk-Neutral)的, ③ 费伦假定排除了一个战争的准充分原因(或者说为什么一 些国家不会坚持他们的谈判立场) ,即有些国家是风险接受(Risk-Receptive)型的。 当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统治着一个国家,并且如果该国正好已经获得了一些重要能 力,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将会引发战争。虽然像希特勒这样的极端案例十分罕见, 但风险接受型的领导人未必如费伦所期待的那么稀有。正如勒博所言,当领导人 面对可能丧失尊严与威望的情形时,他们会变得相当能接受风险。④ 罗伯特 • 鲍威尔(Robert Powell)试图进一步探索承诺问题的根源。⑤ 他声称, 费伦对战争的三种“理性主义”解释最终被解构归入承诺问题中,战争因而仅仅 ①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 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Spring 1996), pp. 91-121; Andrew Kydd, “Sheep in Sheep’s Clothing: Why Security Seekers Do Not Fight Each Other,” Security Studies, Vol. 7, No. 1 (Fall 1997);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Chap. 2. ② Erik Gartzke, “War Is in the Error Ter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3 (Summer 1999), pp. 567–587. ③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 7. ④ Robert Powell, “War as a Commitment Probl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0, No. 2 (Winter 2006). ⑤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58-67. · 35 ·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 是一个承诺问题。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事实上,他的解 释(再次)混合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在费伦的讨论中,我们还隐约可以发现动 机、意图、决心和能力几个因素,而到了鲍威尔的理论中,就只剩下“承诺问题” 的标签了。鲍威尔把战争只当成一个承诺问题的做法从国家的战略计算中掩盖了、 甚至是完全删除了对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① 虽然过分强调意图会扭曲我们对国际 关系的理解,但无视意图的情况更为糟糕——它让我们对现实国际政治中不确定 性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视而不见。 从根本上看,将战争视为承诺问题并不会增加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其仅仅是 将不确定性问题重新贴上了一个并不十分有趣的标签。最后,通过边缘化、甚至 删除意图的不确定性,正式或非正式的理性选择模型最终采取了与进攻性现实主 义异常相似的立场。对于这些理论或模型而言,只有当战争毫无益处,才应该避 免战争。 ② 然而,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这一立场所依靠的基础是十分脆弱的。更糟 糕的是,经验事实全然不支持这一论调。1945 年后国家间实现了大量的合作,但 无论是出于意图的不确定性还是承诺问题的考虑,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理性选择 理论家们都只能或暗或明地宣称 :在世界政治中,只有极少的妥协可以达成。 (四)不朽的慕尼黑,还是被误解的慕尼黑? 在慕尼黑的悲剧中,内维尔 • 张伯伦与爱德华 • 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在 希特勒要求合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之前做出了让步。这让慕尼黑永远与 “绥靖政策”这一声名狼藉的术语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转而使慕尼黑成为了 国际关系领域中最为强大、最多援引并进而被最多滥用的意象之一。可以说,慕 尼黑这一隐喻已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决策者。 ③ 对于许多人来说,慕尼黑的象征 意义是一位野心家可以轻而易举地隐藏其真实的(恶意)意图,因此竞争性的政 策总是比合作更为可取。④ 此外,由于合作姿态(即示善信号)只会让对手变本加 厉, (通过妥协而达成的) 合作总是危险的。因此, 竞争永远是一种更为可取的政策。 区分不确定性五个维度将对有关慕尼黑的一些错误理解做出新的阐明和澄 清。从本质上说,慕尼黑事件存在三种可能的理解方式,而只有其中的一种支持 恶意容易被隐藏这一观点。另外两种理解实则指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第一种理 ①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58-67. ② Dale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也可参见Shiping Tang, “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3 (September 2008). ③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Christopher Layne,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Use of History: Neville Chamberlain’s Grand Strategy Revisited,”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3 (July 2008) . ④ David M. Edelstein, “Managing Uncertainty: Beliefs about Intentions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1 (Autumn 2002). · 36 · 2014 年第 2 期 解认为,慕尼黑悲剧的产生是由于张伯伦没有意识到希特勒的恶意。第二种理解 认为,尽管张伯伦意识到了希特勒的恶意,但他无法确认希特勒的野心与决心实 际上有多大。这一理解并不支持恶意容易隐藏这一观点。其重点讨论的是张伯伦 对希特勒扩张的范围和决心的不确定,而非希特勒的扩张意图。将这一理解与第 一种解释等同就犯了将意图与决心或利益混为一谈的错误。第三种理解则认为, 导致慕尼黑悲剧的原因并非是张伯伦不确定希特勒的恶意或是虽然他认识到了恶 意但不确定希特勒的贪婪程度,而是英国和法国缺乏相应的军事能力进而缺乏在 慕尼黑抵抗希特勒的决心。 ① 同样,这一理解也不支持恶意容易被隐藏这一论点。 近期的经验研究已经很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早至 1934 年,晚至 1936 年,当希 特勒将莱茵兰地区再军事化后,大多数法国与英国的决策者,包括最为关键的张 伯伦本人,就已经得出了德国对欧洲的和平造成了严重威胁这个结论。尽管莱恩 (Christopher Layne)② 、利普曼(Norrin M. Ripsman)与列维③ 、巴罗斯(Andrew Barros)与伊姆莱④ 对导致英国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的确切原因意见相左,但他 们都同意一点,至早在 1933 年,至迟到 1936 年,英国和法国都已经意识到了希 特勒所带来的一目了然且迫在眉睫的危险。⑤ 到了慕尼黑事件发生的时候,即使仍 然很不确定希特勒的野心究竟有多大,英法两国的领导人对希特勒的侵略性与(发 动战争的)决心的不确定已然为零。无论以何种方式衡量,对希特勒意图的不确 定都不是导致慕尼黑悲剧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虽然可能有很多原因使英法两 国没能坚定地去对抗希特勒,但没有意识到希特勒的恶意以及他带来的威胁肯定 不在这些原因之中。尽管希特勒认识到了隐藏其真实意图的价值,但他从未像戴维 • 正如亨利 • 埃德尔斯坦(David M. Edelstein)所认为的那样擅长做这件事。⑥ 事实上, 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早先所指出的,当面对一个类似于拿破仑时期的法国 这样的革命性政权时,常见的错误并非是对意图的误判, 而是低估其野心(即利益) ① 从事后来看,如果英国与法国在慕尼黑打一仗而不是一年后不情不愿地再做这件事,结局一定会 更好一些。参见W. Murray and A. R. Millett, A War to Be W on: Figh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显而易见, 第二种与第三种理解的结合是更为合理的一种解释。 ② Christopher Layne,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Use of History: Neville Chamberlain’s Grand Strategy Revisited,”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3 (July 2008), pp. 404-405. ③ Norrin M. Ripsman and Jack S. Levy, “The Preventive War that Never Happened: Britain, France, and the Rise of Germany in the 1930s,” Security Studies, Vol. 16, No. 1 (January / March 2007), p. 150. ④ Andrew Barros and Talbot C. Imlay, “Correspondence: Debating British Decision Making toward Nazi Germany in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1 (Summer 2009), pp. 173-182. ⑤ 也可参见David M. Edelstein, “Managing Uncertainty: Beliefs about Intentions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1 (Autumn 2002), p. 29。 ⑥ David M. Edelstein, “Managing Uncertainty: Beliefs about Intentions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1 (Autumn 2002)。 · 37 ·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 与发动战争的决心。① 因此,许多人将慕尼黑悲剧理解为表明恶意不易察觉的现实案例是错误的。 这些错误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慕尼黑神话的影响。其所造成的一个关键后果 隐藏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假定之中——因为意图本身难以被估测,所以对于国家 而言更好的做法是将他国的意图假定为最恶,并将所有的妥协都视为“绥靖” 。② 慕尼黑神话因此有力地阻止了国家通过保证来寻求合作,即使合作与竞争一样是 自助(Self-Help)的一种重要手段。③ 六 理论意义 :打倒结构(现实主义)的正统地位 对于国家的动机或目标,从修昔底德(Thucydides)到汉斯 • 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 、阿诺德 • 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的古典现实主义者给了(作为 个人集合的)国家很大的选择自由,从安全、权力、统治到名望与虚荣都是可以 选择的对象。④ 然而,在肯尼思 • 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的结构主义革命后, 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和他们的批评者都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即国家追求生存是一 个最基本的假定,而权力是一种追求生存的手段进而其本身也可以作为通向安全 的间歇目标。⑤ 此外,对于多数后华尔兹时代的现实主义者而言,目标(或动机) 与意图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 :动机受结构驱动(即被无政府状态支配) ,而 ① Henry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 of Peace, 1812-182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7, pp. 2-3. ②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163-164; David M. Edelstein, “Managing Uncertainty: Beliefs about Intentions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1 (Autumn 2002); Randall L. Schweller,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14; Randall L. Schweller and William Wohlforth, “Power Test: Evaluating Realism in Response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9, No. 3 (Spring 2000), p. 81. ③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Andrew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chap. 5. 事实上,不朽的慕尼黑神话所代表的意义(即由于他国的意图是 内在的,一国必须尽早坚定立场)反映了恐惧这一社会进化心理的力量:我们天生给予负面事件更多的 关注,因为我们希望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关于这方面更详细的讨论,参见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Fear (and Trust): Or why i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ifficult?” paper presented in the 49th Annual Con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n San Francisco, March 26-29, 2008。 ④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⑤ Dale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Jeffer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2000-2001), pp. 128-16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38 · 2014 年第 2 期 意图的驱动力则来自单元层次。① 因此,虽然每个国家都在寻求更多的权力与安全, 但不同的国家追求这两个目标的战略是不同的(即是恶意或善意的) 。 这种由华尔兹启迪的正统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启发了对国家行为与结构性结 果的理论化。 ② 然而,套用麦克唐纳的话,这一正统只是“有用的虚构” (useful fiction) ,③ 而非“奇迹制造者” (miracle maker) 。④ 因为正统仅仅是“有用的小说” , 其最终会弱化并误导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所以应该被坚定地予以拒绝。 尽管很多人相信是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对他者意图的不确定性,但无政府状态 与对他者意图的不确定性之间并没有内在联系。对他人意图的不确定无所不在, 即便是在等级制国家内的日常生活也如此。 更为关键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国家想要的不仅仅是抽象的安全与权力,而 是切实的物质的和象征性的事物,比如特定的领土、可度量的货币收益、明确的 投票份额、面子、威望、荣誉等,并且后一类的情况更为多见。因此,在现实世 界中,将安全与权力的抽象概念作为目标对于把握国家真实动机的帮助是很有限 的。政治家们(其他人也是一样)希望知道其他国家想要的是这样或那样的确切 的东西,而非“安全”或“权力”这样的抽象事物。坚守国家追求权力或安全的主 张削弱了国家利益天生拥有的对国家行为的解释力,而这种解释力已经体现在马 基雅维利的至理名言中(即“目的是手段的理由”) 。很显然,不同的目标通常需 要不同的能力、意图和决心。 为了理解真实的国家行为,我们必须探究国家的特定利益诉求。显然,如果我们 仅仅坚持国家追求安全与权力这一个观点,便不可能理解为什么朝鲜与越南北方都如 此致力于实现民族的统一。我们必须承认,金日成与胡志明都是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民 族主义者,而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兴起也预示着由他们二人所领导的国家将会 被狂热民族主义强有力地驱动起来。从反事实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的精英们将这两 场战争建构为民族统一的战争,他们定然远远不会觉得自己必须要介入其中。 ① Robert Powell,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Neorealist-Neoliberal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Spring 1994), pp. 313-344; Jeffer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2000-2001), pp. 128-161;也 可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91-92; Charles L. Glas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2 (July 1992), pp. 497-538, esp. 499-502。 ② Benjamin O. Fordham, “The Limit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Additive and Interactive Approaches to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Preferences,” in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51-279. ③ Paul K. MacDonald, “Useful Fiction or Miracle Maker: The Competing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7, No.4 (November 2003), pp. 551-565. ④ 事实上,就连华尔兹自己也无法明确说明他的这些假定在工具性层面是必要的,所以只能称之为 “为了建构一个理论而采取的比较激进的简化”。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91-92。 · 39 ·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 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国家行为(这也是新古典现实主义所宣称的目标),就 不能仍然只听从这种结构正统。① 事实上,国际关系学者的主要任务是把动机(或 利益、目标)作为国家行为的主要驱动力来进行解释,而不是通过假定国家追 求权力与安全来将这一问题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没有对驱动国家的有形目标 的一定了解,便无从充分理解国家的行为。格拉泽 ②、施韦勒 ③ 等现实主义者开 始试图将所有的动机纳入相关的描述之中。他们起了个好头,但做得不够。沃 尔福思认为国家安全存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 ④ 这一根本性的洞见意味着我 们必须将哥本哈根学派与社会建构主义共同纳入我们的分析和描述中。国家利 益并非是由结构赋予的,而是由精英(以及公众,不过相比之下作用远不如前者) 通过叙述中的话语行为建构出来的。 ⑤ 在此过程中,文化因素需要纳入到描述 和分析之中,因为社会心理学家们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文化因素确实影响着 社会认知,包括归因。 ⑥ 在此意义上,哥本哈根学派与社会心理学对于结构现 实主义(以及结构建构主义)来说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挑战,还是一种必要的 救济,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国家利益的渠道。 同时,国际关系领域的心理学研究的最大挑战之一,在于将心理学和大的 研究议题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建构主义对身份与身份变化的强调显然是一块试 验田。然而,多年以来,众多的建构主义研究文献同样过于结构化,并且一同忽 视了所有的心理因素。如果说主要采用物质主义路径的现实主义或许还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承担得起忽视人类社会中观念变化的现实过程及观念的变革的力量的代 价,建构主义却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其所宣扬的正是观念的变革之力。因此, (没 有心理学的)结构建构主义是自相矛盾的。我们需要建立起连结宏观社会(物质 的与观念的)变化与心理变化的桥梁。另外,从安全化(或去安全化) 、社会习得、 建构到群体认同、哥本哈根学派、社会建构主义与社会心理学所强调的所有的过 程影响国家目标界定与战略选择的关键途径都是国内政治。因此,要充分理解他 国的行为,建构主义同样必须开始认真进行对国内政治的研究。 ① 参见Steven E. Lobell, Norrin M.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② Charles L. Glas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2 (July 1992), p. 507. ③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7. ④ 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67, No. 4 (December 1952), pp. 481-502. ⑤ Ole Wea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D.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6-86. ⑥ Richard E. Nisbett, Kaiping Peng, Incheol Choi, and Ara Norenzayan,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108, No. 2 (March 2001), pp. 291-310. · 40 · 2014 年第 2 期 结构正统是一种作用很有限的工具,其为国际政治描绘了一幅不完整、甚至 扭曲的图景。它“辉煌了”30 年,现在是我们同它彻底决裂的时刻了。 结论 :超越国际关系的归因 不确定性的研究理应在国际关系以及其他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核心 位置。在国际关系中,在对不确定性的既有探讨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由社会心 理学的认知研究(尤其是其中的归因理论)所支撑的。然而,尽管近期取得了一 些重要进展,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研究在理解现实世界政治方面是不令人满意的。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并未区分上文所提及的五个维度,也没有涉及五个 维度间的动态互动。而且,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情形往往在实验中受到控制,其 通常远远比现实政治中的情况更为简单。这样的结果就是,国际关系中对不确定 性的现有研究往往是未作区分的、非系统性的以及静态的。 本文中,笔者提出了一种针对国际关系的新的归因理论,而这种归因理论也 能够从几个方面对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学归因研究做出贡献。首先, 其对行 为的各种动因做出了更为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其次,通过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 即我们的归因受控于群体动态的影响,这一理论还指出了一种将个体主义与集体 主义结合起来的归因研究路径。再次,这一理论要求使用更为系统与动态的方法 来研究归因,并将个人与集体的历史、身份以及话语引入到相关讨论中。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家从不吝于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不幸的是,社 会心理学与政治科学或社会学之间的对话常常是单向的 :社会心理学家几乎只在 彼此间汲取灵感。然而,通过向政治科学家与社会学家学习并与之合作,社会心 理学家们可以收获许多的东西,因为前者对个体(从关键决策者到选民)在重要 的现实生活情境中如何思考与行动知之甚多。因此,我们也需要心理学家从国际 关系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科学与社会学研究文献中吸纳和借鉴。毕竟,如果 只拿大学二年级学生做实验,社会心理学不可能获得自身的发展与成熟。 为了在社会心理学与政治科学或社会学之间形 成双向对话,我们同样需要国 际关系理论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去建构能够同时被实证和实验所论证的心 理学理论。只有这样,国际关系理论家才能在理论上对社会心理学做出贡献。本 文在此方向上迈出了一步。① 【来稿日期 :2013-10-10】 【修回日期 :2013-11-10】 【责任编辑 :谭秀英】 ① 勒博对前景理论的重构指向一个与此相近的方向。参见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4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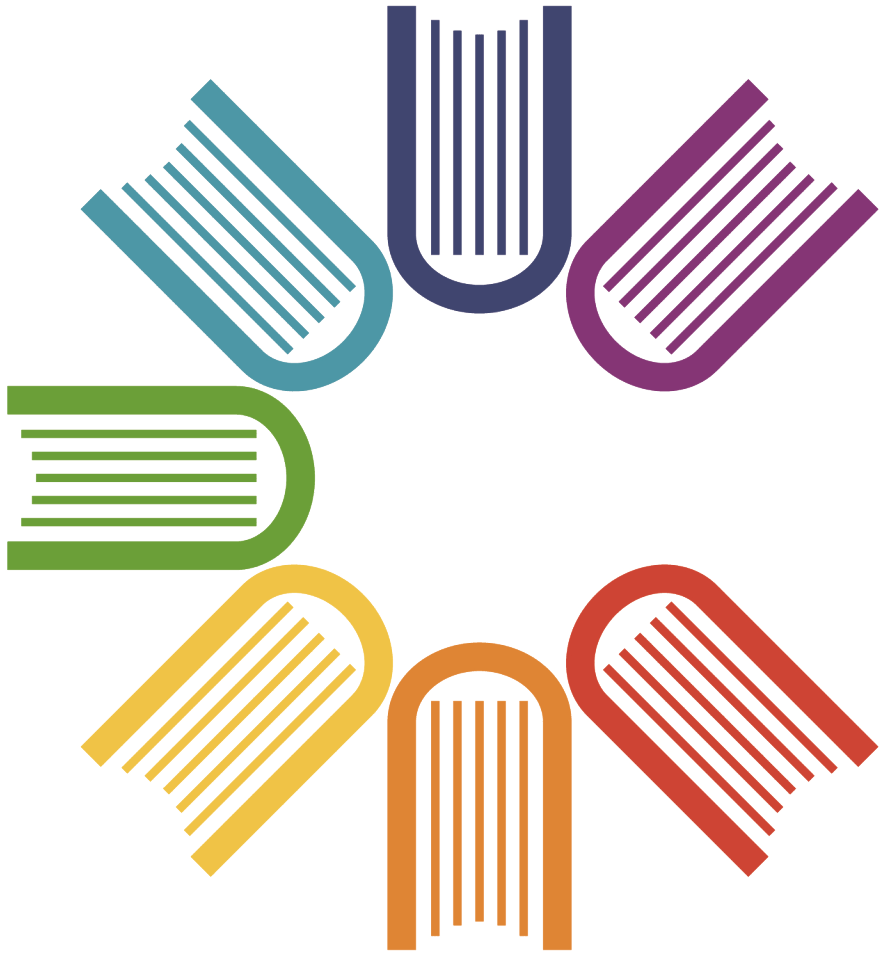
 唐世平: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pdf
唐世平: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