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头牛的惨剧.pdf
四十头牛的惨剧 一九三三年夏,我旅行到了云南边地的怒江流域。 连续了四十多天的长雨,和因淋雨太多而起的骨节冷痛的风湿症,把我困居在一个名叫 阿育乐地的黎苏小村中。那里只有四五家人。 雨是没一刻停的。白雾的幕,雨的线条,整天可看得见的就是这样单纯忧郁一个天空。 我来的那天,遍身都淋湿了雨,席地坐在火炕边想用柴火来烤干这天天都要淋湿的衣 服。正和我们一路经过的黎苏寨子一样:照例,这小村的人亦全围拢来呆看我们。 是汉人哩!不懂事的小孩们指着我们用惊奇的眼光说。于是有较大一点的男孩拉拉他 们的衣角轻声说: “说不得的!快回去!妈妈喊咧! ” 我微笑地看着他们说的与被说的都呆呆地望着我,任一方面都不走。 有的是一碗米,有的是几张菜叶,有的是几根小柴枝,他们陆陆续续地走了进来,搁 在门角后,就算是为我这客人送了礼物了。随后就悄悄地走拢火坑,斯斯文文地坐倒在地上。 “这叫什么?那是什么?”用生硬的黎苏话问他们各种家俱的名字,就算是我对他们 的寒暄了。 他们逐一回答。又称赞我学习的能力。 笑眯眯地门上出现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满身滴着雨珠,背了一箩的柴。揭下笠帽, 放下柴箩,他带着笑到火炕边的人群中蹲下。 “冷啊——冷啊!”他含笑说,搓手向火。 他从一个专门挂着装烟的长方布袋中掏出一枝烟杆,装上一撮还没有晒过的绿色烟叶, 就火吸起来。 于是怪味的烟就来为难我的嗅觉。 他很美。黎苏中实在很少看见像他一样的清秀的少年。他无邪的笑容,他没有皱纹的 面部,他清白的口齿,都使我感到他在黎苏中是一只独出的白鹤。 自幼小便起的体力劳动没有在他脸上刻起皱纹——这是奇怪。 每年都有几天的饥饿没有消灭他口角上的微笑——这也是奇怪。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我吗?我是华阿思!你呢?”他笑着。 有点茫然了,从来没有黎苏倒转来问我的名字过。 “叫爱克司” 。我欺蒙他。 “你卖些什么?”他指指我的皮箱问。 “卖药,各种的药。打摆子的药,尿血的药。你们拿鸡和鸡蛋来跟我换罢。” “爱克司,哈,爱克司! ”围着火炕的人群都在当作新鲜话头儿念。从此爱克司成了我 的称呼。 “娶媳妇了吗?” “没有没有哩! ”他摇摇头笑。 然而单另有一个男孩——那是一个脸很脏的——用手指指一个坐在暗角上的女人装鬼 脸。 很暗,我瞧不清楚脸貌。洁白的牙齿从暗光中显了出来,我隐约能尝味到一个美丽的 笑脸。 “几条黄牛讨来的?”我嘻皮着。 用手掩住嘴,他暗示我不要说,好象是有某种说不得的理由在。 “她会害羞的哩!”低声通知我。 “格格,格格……” 像被人搔着痒似的笑声,发自暗角。 ——啊!是都市里的姑娘的笑声啊! 我惊异地辨味出这样像混在回忆中的气息来。 “来哟,来向火哟!”我招呼她。这种对陌生女人的大胆,我以前在都市中是没有的; 不过到了怒江——这还在原始社会的黎苏地方,姑娘是没有所谓文明女子的守身如玉尊严的 ——我想,任何懦怯的男子也不会感到心头的压迫罢。 还是格格的笑,她停了手中理着的麻线。但不来。在暗光中又被我发见在洁白的牙齿 的上头,闪灿出一对黑亮的圆眼睛。 ——到底是怎样一个女人呢? 我十分想看她的面庞——能发出如此都市气的笑声的面庞。 “不来吗?我会使你来!” 但他还是格格地向我笑,但有些微醉似的,骤地站立起来,跑向她所在的暗角。 “不去吗?我要拉你去!” 她还是格格地笑,不起来。于是实行所说的话,去拉她。 像拉一个懒软了的猫儿,动也不动,我只听见耳朵边格格的笑声。脸红了,这是耻辱 ——哼,一个男人拉不动一个动人! “哈哈,哈哈……”是背后笑声的总攻击。 涨红了脸,涨红了脸——哼,一个青年小伙子拉不起一个女人! “起来吧,客哩!”不知谁在说。我感谢他! 有效!她笑弯了肚皮起来了。我用不能以为荣的胜利牵她坐到火炕边。 阴暗的弱光中,火光熊熊地在她脸上跳跃。 ——是张美国影星的脸啊!是很熟悉地袭来的印象。找吧、找吧,到脑中的 Album 里 去翻。 ——Clara Cow?Janet Ganor?不,都不像,却又好象都有一小点儿像。 也不必一定要找出一个人名来说是她所像的,总之,她有一个电影明星型的圆圆的脸 儿罢了——在穷乡辟野中,看见了一个影明星型的圆圆的脸,听见几声都市的姑娘的笑声, 是有着旧雨重逢的愉快的啊! “黎苏女人不好看吧?那样大的脚,也不裹。裤子也没有得穿,你看,麻布的裙子?” 她指指赤着的脚,又指指折叠很多的裙子,说。 我在注意她那双每次用来帮助说话的很活泼的眉毛。她见我没有话,就把插在盘头发 辫上的小烟杆取下来,装上烟叶,就火炕中的火“啪啪”地吸起来。 我也从衣袋内取出烟匣,拿一枝纸烟挂在自己的嘴上,又递了一枝给她。 “什么哟?” “烟! ” 我把自己的先点燃吸着。她也带着点不相信的神气吸她的。看她皱起眉心一半害怕地 吸了第一口,仿佛小孩子咽下一口苦药似的。我猜测她是要把纸烟丢掉了。但是当她轻轻地 喷出一朵烟的云,小孩似的笑容上的眉毛弯得像湖上的新月了。 “啊波! ”她用黎苏惯用的感叹音说:“是又甜又香的哩! ” 于是她再送给我一回湖上的新月,和一个活泼小孩才有的笑。忽然她又想起了什么急 事似的,突然回过头去,把纸烟递给华阿思——她少年的丈夫,说: “你也尝尝这。” ——这幅递烟图给吉士烟做广告画多好!望着户外白雾的幕和雨的线条,在心中轻轻 地这样赞叹! 从此便日日看见这一对小夫妻。天一亮就起来,男的用一只脚滑着樁米,女的坐在一 旁筛糠。粗糙的木制杵臼“得格,得格”地响着简单的太平时节的调子,他们老是唱一些滑 稽的小曲子互相谑笑。我听不明白曲子里的话语,但听得出那是一些愉快,一些天真! 天天这样的,樁一顿的米煮一顿的饭,从不知道多樁一点留着预备下一餐吃。吃了饭 就背着大箩上山砍柴,我在家也听得他们“噹噹”的斧砍木头声,歌声由远来近的时候,就 是他们由山上回来的时候,他们两口子总是抱一上扎柴来送给我烤火,或者带几个鲜嫩的玉 蜀黍来和我在火坑中烧了吃。我呢,总每人拿一枝香烟给他们吸。每次看看他们一点阴云也 没有的笑容,就把困居穷乡的寂寞忘记了去。 熟了,便慢慢知道了他们的恋爱故事。 原来她——她的名字像所有黎苏的长女一样,是叫作阿娜——是高黎贡山那面,现在 已属英国管领的恩迈开江的人。她先就照着黎苏的传统十二岁时嫁给叫阿次的男人。由她父 亲收了二十条牛的聘礼——计活牛九头;十六个拳头高的大牛二头,十二个拳头高的小牛七 头;又死牛十一头:即大锅三口,支铁锅的铁三脚两个,坛子四个,蓝布四匹“每二匹抵死 牛一头。”婚后,阿次和阿娜的感情十分好:他们每次到亲戚人家做客总是要一同去的。路 上阿次佩着腰刀和弩箭,提着装酒的竹筒,挂着装烟的口袋;阿娜背着一点铺盖之类的物件。 酒吃够了,两人一起在火炕边对跳他们的 Cnia-hon-chia 舞。阿次不会和旁的女人跳,阿娜 也从不会去听旁的小伙子吹笛子。醉了,累了,大家一齐倒在地上。阿次总爱把头枕在阿娜 的肚皮上,模模糊糊地哼一些醉后忘情的调子。 有一天,又是逢到一家亲戚因为丰收请亲朋们喝酒的日子。阿次照例喊阿娜一同去, 但是阿娜说玉蜀黍熟了,怕松鼠或雀儿会来偷吃,她要到山上去看守,不能去。叫阿次独个 去。阿次走出门,听阿娜在门口喊:“他家预备了一大锅的山耗子肉,你要给我带些回来的 啊! ” 这天,阿娜在烈日底下吆赶来吃玉蜀黍的松鼠时,总是骂: “小谗嘴的!瞧阿次带着烫 了毛的你回来!” 下午,饭也不煮站在门口等候阿次转来,要吃耗子肉。可是阿次转来时天已出了月亮, 而且是大醉了。 “耗子哩?”他坐下在火炕边时阿娜望望他的醉脸这样问。 “阿哟!是遗落在路上了罢。”他醉了的冷寞的声音。 “遗落?好,那末你跑回去寻找来给我吃! ” “天黑了,哦,说不定给野狗衔去了,哦哦……” “野狗倒衔不去,怕是给了野女人衔?” “不会的,不会的,哦哦我……累了,醉了。 ” 男的倒下在火炕侧边,瞌上眼皮,是要睡了。女的先是没有耗子肉吃失望,后又疑心 到男子有不忠实的行为上去,愤慨得要哭。她需要男的用话来安慰她,用温存的话证实没有 女人能够代替她吃他手上的耗子肉。即使那些话是编造出来的,她也会满足。 可是他醉了,累了,他瞌上了眼皮。他不去填塞她疑妒的窟窿。 她先是拿质问去想赚得他坦白的证实,他瞌着眼皮。继又用哭泣去想赚得他温存的安 慰,然而他的醉脸在吐着口沫,终于她哭出声气来,不可抑制。 从醉梦中被惊扰过来的他,怒了,大声地嚷: “算了吧?哭你老爹的坟! ” 她是觉得受了更大的冤屈,大哭。用手去抓住他的肩膀,拼命摇,哭着问: “谁是小娼 妇?谁个小娼妇吃了你的耗子肉?啊,你丢掉我吧!” 这一摇,摇出了他一半还在醉梦中的火,鼓着眼珠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顺手去火 炕里抽出一块燃着的柴来,往她胯子上一搠,叫声:“死你的! ” “A-moa-mo……”她双手按住小腹喊。 他鼓着眼珠看自己所做的事。一回儿,觉得还是累,又倒了下去。 她倒反而哭得像没有声音了。一回儿,撑着手支起身体,一步一步地,跛着腿,走出 门口去。当晚摸了四十里路,回到父亲家中。 第二天,她一早起来为父亲樁米,为父亲煮饭。她向她父亲说:“你的女儿转来了,她 依旧做你的女儿。” 过了五天,从阿次的村中来了二十几个人,走进阿娜的父亲家,一句话也不说。就大 家自己坐在火炕旁边。 阿娜的父亲知道是来评理的,也一声不出;却赶忙到邻居去借了一坛酒,又杀了一头 黄牛。 一点也不提起,大家冷着脸孔。围坐在炎炕边大嚼。酒甜,来的人中有一个老者开始 冷冷地发话: “你的女儿跑转来了。” “是的。 ” “但是她是阿次家的人,她该回去。 ” “她被虐待了,你们看她被烙伤了。她不肯回去。 ” 突然二十多个人都喧闹起来,醉了的脸,口中说话时吐出口沫。 “但是她是阿次的老婆啊!” “阿次要她回家中煮饭,织麻布。 ” “阿次是出了二十条牛讨她的啊! ” “不能收了人家的牛,又喊回自己的姑娘。 ” “把她拉回去,强迫她回去!” 众议纷纷,一直到了天亮。 结果是阿次的父亲和最先讲话的那个老头子慢慢地磋商了如下的离婚条约: 一、从此阿娜另嫁,阿次另娶,两不相干。 二、阿娜的父亲须偿还阿次的聘礼牛二十条。 三、另给阿次损失费牛二十条。 四、以上共需赔牛四十头,阿娜何日找得丈夫,何日即为交付日期。 五、在阿娜末找得丈夫之时期内,阿娜每年织麻布衣二套,送给阿次穿。 这样协定了以后,阿娜一直和她父亲住在一块儿,直到怒江的华阿思今春去恩迈开江 做生意——拿盐或布匹去交换黄连,贝母等药材。 他和阿娜一见便成天生的一对儿,后来呢,便得意地带回怒江来。然而这姑娘的代价 是四十头牛啊——这美丽的姑娘。 黎苏原有一种传统的美德,一村中人,谁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只要你有本事领得旁村 的姑娘来,牛是可以向同村的邻人借集的。谁一个人能一时出得起几十条牛?现在我娶亲, 你借我一头牛,挂上账吧,那天你家儿子长大了,我再还你,不好吗?但是华阿思住的是山 谷中的一个小寨子,只有四五家人,怎样筹得出如此的巨额,四十条牛? 阿娜一走,阿次便逼着她父亲要牛;他要了牛去,可以赶着进任何出奇的姑娘底父亲 的牛棚内,而受欢迎。他村中的代表们宣言,交出牛来或交出人来,否则他们要动武。 ——啊,离婚要赔偿损失。结婚,要资本。无论什么人类在的地方都放好这个圈套叫 你去钻,甚至在如此一个原始时代的,古风十足的区域里。我是把思绪旅行到都市新闻纸上 的许多社会新闻上去了。 但是阴去从来没有遮住过他们的笑容。每次,我买酒来请他们喝的时候,他们欢跃得 如一对感恩的小狗熊。我也曾看见过,他们快乐得抱住作惯跤的玩意儿,他们教我唱黎苏歌, 我学会了那首“没烟吃的时候” : “没有烟吃的时候, 撮把树叶来吸吸吧; 没有妻子的时候, 折朵野花儿来戴戴吧。” 然而我是一个读过债权法的人。当每次看见湖上的新月上升,和从来没有阴云的笑容 出现时,总是这样想: “牛啊,四十头牛的代价啊! ” 这是有一天早晨,阿娜面色庄重的走了进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走着这样深沉徐缓 的步调。她后面还跟着一群的小孩子。 弯弯的新月下面的黑眼睛不见了,换了一双忧郁的有雾光的眸子。不看人,只痴望那 户外白雾的幕,和雨的灰色线条。她口中唱着,低低地唱着,寂寞但是庄重的长曲子——听 去像欧洲古代的长史的长史诗一样。我好像看见了一个修道院里的处女在虔诚地祈祷。 她脚下轻轻跳着黎苏们的小舞——他们叫它为 Wo-kai-kai 的。声音沉长得像背诵悲壮的 欧洲古代的长史诗一样,那样一句一句地徐缓吐出。Wo-kai-kai 的步调是那样的幽静,每印 一个脚印在地板上便像是一个处女的轻微的叹息。我好象看见,她,就是那个因犯了奸淫在 胸襟上绣上了红十字的妇人。 ——她是一个女巫吗?她大概是在念什么送鬼神的咒语吧?我猜想。 “她疯了,疯了!”不知在什么时候,华阿思已默默地站在我身旁,丧了脸说。 “怎么?” “她父亲被原夫村中的人掳了去做农奴了! ” 看看阿娜,悲哀从她有雾光的眸子中透出,悲慨的。疯了吗?这是一种对我的脑子陌 生的疯,我只觉得庄严和诚虔。她出神地在唱。我只抓得住几声零片: “…… 那晚妈妈…… ……你们这些强人 …… 爸爸…… 爸爸,逃跑…… …… 英国的官…… 我背着你, ……树林里。 ” 我紧紧地闭着嘴唇。还是 Wo-kai-kai 的步调,还是诵诗一样的长音。看看四周的人,都 像穿了黑衣去送丧似的沉默。 忽然,华阿思无邪的眼光对了我,是很恳切的声音问: “爱克司,你可带得有医治这种病的药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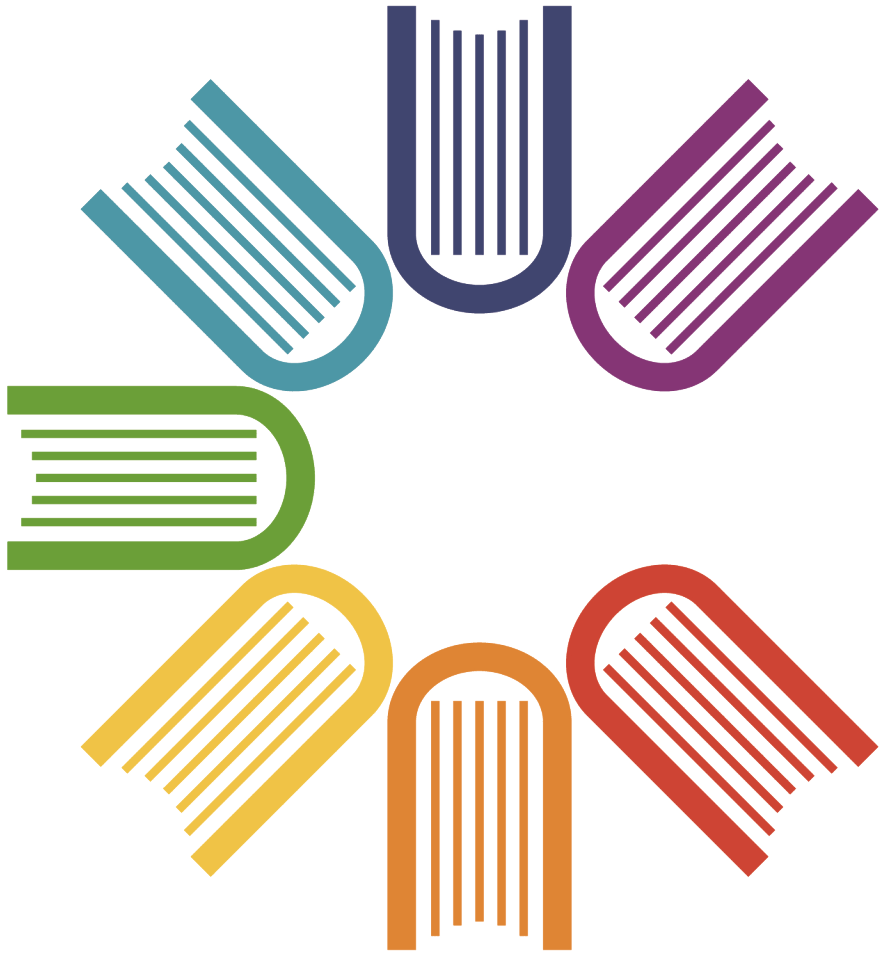
 四十头牛的惨剧.pdf
四十头牛的惨剧.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