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马塞斯:文明的回归.pdf
文明的回归 专 题 文明的回归 Focus [葡]布鲁诺 · 马塞斯(Bruno Maçães) 李 沅 译 文明国家的重现,正带领我们超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塞缪尔 ·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著作常被认为专注于文明研究,但他在其中真正讨论的是身份认同。这两个概念 大相径庭,且对两者的混淆恰恰解释了为何亨廷顿会主张俄罗斯和乌克兰属于同一文明。因此, 他认为两国之间基本不会发生任何冲突。尽管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因同为东正教徒而拥有某种 共同的宗教认同,但这场乌克兰危机则揭示了民族国家认同在世俗世界中的优先性。 一边是乌克兰人正为了保住乌克兰的国家地位而战,另一边则是普京公开宣称如果乌克兰 得以幸存则俄罗斯将难以生存。在危机的动态变化之上,两国都在缓慢倒向各自的文明型世界, 其植根于不同的历史、情感以及最终形成的迥异政治理论。在俄罗斯,皇权的遗产延续至今, 这使其与中国走得更近。而在乌克兰,哥萨克(哥萨克一词本意就是自由人或冒险者)的自由 与独立理念可能会很快将其带回到作为欧洲政治传统一部分的应有之位。 正如哲学家弗拉基米尔 · 叶尔莫连科(Volodymyr Yermolenko)曾提出的,现代乌克兰文 学起源于伊万 ·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Ivan Kotliarevsky)的诗歌《埃涅阿斯纪》 (Eneida)绝非巧 合。这是一部以乌克兰本地语言对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史诗《埃涅阿斯纪》 (Aeneid) 的诙谐改编诗作。诗中将埃涅阿斯及其特洛伊同伴的故事替换为乌克兰哥萨克,从而将乌克兰 历史锚定在罗马创始神话中。 16 世纪,乌克兰哥萨克以类似西欧贵族限制君主权力的方式,从诸多东欧统治者那里获得 了某些权利和自由。正如乌克兰小说家安德烈 · 库尔科夫(Andrey Kurkov)喜欢指出的那样, (1) 哥萨克选举酋长(Hetman) 的传统让乌克兰人更习惯于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而在俄罗斯,人们 则相信沙皇是“真命天子”。 让亨廷顿及其他一些学者[如几个月前在《纽约时报》撰文写道“是的,存在一场文明的 冲突”的罗斯 · 多赛特(Ross Douthat)]所无法理解的是,文明与身份认同之间是存在区别 的。文明需要与其他概念(诸如宗教、种族或国家认同)区分开来。前者是一种出于政治原因 的实践,是一种围绕我们与真理、与世界以及与彼此之间基本关系的准则而开展集体生活的努 力;而身份认同,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是自由主义特有的东西,是文明残缺不全的尸体。 文明国家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为社会和政治生活提供一个总体框架,因此是西方自 由主义的可行或合理可信的替代方案。文明国家是一种直达集体性存在最深层的基础性概念。 (1) 在哥萨克酋长国(Cossack Hetmanate)时期, “酋长” (Hetman)是一种职位,担任该职位的人由选举产生,为终身制,享有最 高军事权与首席立法权,实际作为哥萨克的国家最高元首。1764 年,该职位被俄罗斯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除。—译者注 33 东方学刊 2023 年 3 月春季刊 专 以以色列和印度为例,如果成为文明国家,它们生机勃勃的使命将分别是组织、发展古老且多 题 样的犹太教和印度教传统。它们会给世界和人类的某种愿景赋予生命。照此理解,文明国家可 能确实是拥有特定领土和民族的,但真正定义这个国家的在于其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幻想同一 Focus 族群世代定居于祖先留下的土地,不符合文明国家的逻辑。 “文明”一词本意在于表达一种与更原始或自然状态下的生活相对立的政治或社会存在状 态,后来,这一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原则为集体生活提供了基础。但随着自由主义的兴起,文明 在这一意义上受到了抨击。有人可能会争辩,文明国家的政治永远植根于某种排他的或特定的 观点,而自由主义则可视作其替代者。自由主义抨击文明国家的生活是饱受制约以及贫穷的。 毕竟,如果一个国家是围绕某一特定观点组织起来的,则它一定是排斥其他可能性的。 自由主义者梦想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国家,一个允许无限可能性的国家。自由主义的国家 有两方面的优势:它承诺提升个人体验所带来的价值,每个人都体验许多不同的“人生设计” 并且了解很多相反甚至矛盾的思想体系以及实用理念;与此同时,一个承认所有世界观可能性 的国家可能会充分接纳生活在其国境内的每一个人,而不计较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或哲学观点, 通过此种方式以终止内乱。 自由主义的卖点也很简单—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国家是保持中立的,因此,每个人可 以是基督徒,也可以是穆斯林或印度教教徒。组织形成政治权力的法律和准则将保持中立,它 们也不代表任何世界观与人生观。简言之,它们不会是任何一个文明的化身,会保持自然、公 开透明甚至是非文明的。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大胆却又古怪的野心。 自由主义者希望他们的政治价值观被普遍接受,就像科学理论一样成为普遍价值。为此, 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对其进行抽象和简化,就像牛顿和爱因斯坦从先前的物理理论中提炼出 了更具形式化的物理关系系统。西方文明不再是个文明,或者说至少它不再视自己为一个文明。 它不再是丰富多彩的传统、观察与审视方式的体现,它放弃了追寻哲学与宗教的古典主义愿景。 它的准则本应是广泛而正式的,而现在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关系框架。 这就是自由主义错位的野心,是注定要失败的。自由主义方案的失败意味着政治不是一门 科学,也绝不可能成为科学。价值中立在理论上听起来很美好,但人生是在有限的时间尺度中 展开的,其间,我们势必要将赌注下在某些对世界特定的理解之上。跨越时空的真理在这里并 不见效。 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由数以百计的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些国家被政治边界界定, 相互对抗,并时常依赖居于统治地位的暴力意识形态。这是自由主义所谓“普世价值”的产物, 或者说是其残余。 你也许会说,起初在 19 世纪,民族主义是用来推翻旧君主制或教会的工具。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民族国家显然永远不会让位给自由主义国家。自由主义希望建立一座属于理性和逻辑的 永恒大厦,但事实证明,它没能在大范围内实现共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仍然对社会生活 中那些无法适用理性的粗暴现实无能为力,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宗教和种族偏见,这些也 不过是冰山一角。 这些没有被自由主义理论同化的政治生活元素,自然被归入感情或传统的非理性核心中, 并因不同政治单元而异。文明国家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解释这些元素,就像许多关于政治和社 34 文明的回归 专 会生活的观点一样,文明国家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解释这些元素。文明国家是建立在思想上的, 题 而非“血缘和土地”上。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明国家的回归早在 19—20 世纪的犹太思想家那里就有所萌生。列奥 · 施 Focus 特劳斯(Leo Strauss)等学者渐渐开始质疑犹太复国主义学派里自由主义的愿景。自由主义国 家未能保障欧洲犹太人的安全与尊严。它不仅没能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也似乎无法兑现其承 诺的犹太人得以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实现自主,免受异化的恐惧。即使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 多 · 赫兹尔(Theodor Herzl)是一位不甚完美的导师,我们仍旧可以从这些一两个世纪前的争 论中发觉以色列萌发出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想法。 正如犹太教保守派会指出的,没有理由让犹太传统适应自由主义,应当反过来。毕竟,犹 太教有数千年的历史,而自由主义最多只能追溯到两三个世纪前。在印度,这一论点也常常被 提及。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论点。 紧要的是,我们至少应该摒弃每一种政治价值都是自由主义传统的观念,并且停止否定敌 对传统的价值。几千年来,犹太教和印度教都发展出了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多样性问题和社会冲 突。如果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无法从那些传统中学习到任何东西,抑或说我们只能等待西方的宽 容价值观才能看到最终的曙光,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如今以色列和印度的主要挑战和任务是把对自由主义的反抗变成一个文明的而非民族主义 的方案。伟大的印度教徒和哲学家斯瓦米 · 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曾经说过,莫卧 儿王朝的第三位皇帝阿克巴(Emperor Akbar)可以被看作“事实上的印度教徒”。显然他是一 名穆斯林,但他所代表的广泛的精神和政治秩序体现了印度教传统里的原则和印度教理想的一 致性。可以想象,穆斯林可以生活在印度教文明国家,就像印度教徒可以生活在穆斯林文明国 家,只要我们心里清楚文明国家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别。 文明不是身份认同。不同文明间有相互接触的领域。伊斯兰传统对印度教文明国家产生了 深远影响,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和阿拉伯或非洲的穆斯林并不相同。在离我们更近的时代,孟 加拉国诗人卡齐 · 纳兹鲁尔 · 伊斯拉姆(Kazi Nazrul Islam)或许可以被看作印度教生活方式 的穆斯林(Hindu Muslim)。纳兹鲁尔生于 1899 年,终其一生都是穆斯林,但在许多方面,他 却能够超越宗教,致力于更加远大的愿景。他在诗歌中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同时也杂 糅了孟加拉语和梵语。人类的语言或有不同,但世界只有一个。 文明国家植根于充分发展的政治哲学,而非种族或国家身份认同。就如何更好地构建政治 社会而言,文明国家倾向于超越宗教信仰,并采用理性思考的方式。但与自由主义相反,文明 国家对终极真理避而不谈。文明国家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它既与自身矛盾对话,也与敌对文明 进行接触和交流,成为更广泛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尽管能从当代中国看到自其前身的延续性, 但如今的中国作为文明国家显然已与过去颇为不同。 为什么亨廷顿忽略了文明的完整特征?最直接的原因是他观察的文明已经过了鼎盛时期, 残存的只是一些文化表现形式。自由主义让这种困境变得更加糟糕,而亨廷顿依旧从自由主义 霸权的角度来写作。在自由主义社会中,其他文化被降格为平凡无奇的表现形式,这在对外国 美食或民族服装的兴致勃勃中可见一斑。亨廷顿考量的正是这种已经衰落的文明的意义。 在世界政治中,文明之间更多的是交流而非冲突。有些文明想要取得全球霸权是很自然的 35 东方学刊 2023 年 3 月春季刊 专 事情。它们会扩张和征服,常常向敌对的世界观宣战。但它们也会改变,因为每一种特定的文 题 明都必然会被迫面对其他选择,并应对它们带来的挑战。 在自由主义之前,世界体系往往被敌对国家间的利益纠葛以及脆弱的共识支配。共同原则, Focus 而非普遍原则,为世界体系提供了共识基础。因此,那些促进共同思想发展的文化交流实践就 显得弥足珍贵。如今,不同的身份认同是排他的,它们相互对立,对话更是天方夜谭。 信徒或狂热者可能乐于见到某个文明成为普遍的存在,但有真知灼见的人明白,每个文明 都必须深度发展,如果它试图扩张成为普遍的存在,实际上将会瓦解。在一个由文明国家组成 的世界里,全球统治性的原则类似于权力均衡。 对文明国家的另一个误解是文明国家存在且只能存在于西方之外。也许中国、印度和土耳 其会回归古老的文明概念,但自由主义将会在它的发源地继续存在甚至繁荣。按照这种观点, 未来将是西方自由主义和文明国家之间的竞争。 笔者不同意这个观点。自由主义的形式逻辑和现实吸引力都来自它的所谓“普世性”。自由 主义一旦成为地域性的事务,它就不再是自由主义了,它不可避免地会演变成自身版本的文明 国家。 今天,每个对欧洲大陆怀有野心的欧洲政治家都热衷于谈论欧洲的价值观,并毫不避讳地 宣称欧洲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这些都只是文明的想法。欧洲的价值观无疑与自由主义遗产相 关,但它们让我们回归其文明核心。它们植根于一种关于世界和政治生活的独特理论,并且充 满了智慧和道德内容,与敌对的理论有明显区别。 当欧洲人谈论规则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神圣作用时,这些都是具体的愿景,其有效性永 远在争论中,其吸引力具有哲学和个人特质。它们有助于理解自然世界,并为日常生活的所有 事情提供指导。 总而言之,对印度人或中国人,欧洲的价值观是众多理解世界的方式之一,甚至也许对美国 人(至少是那种摆脱了欧洲文明观的美国人)来说,这种方式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乃至无法理解。 如果人们试图推测欧洲文明在失去对普遍自由主义的信仰之后会如何,最可能的答案是, 新的文明将建立在欧洲传统中与自由主义最不对立的那些元素之上,因此更可能幸存到自由主 义胜利的时代,并且或多或少地不受损害。文明国家会随着时间演变,而这种演变无法摆脱路 径依赖。法治观念在某种形式上是由罗马人发展起来的。有人认为,对自由主义中立性的最好 理解是法治的一个极端变体。这个变体也可能再次被原版替代。基督教长期以来都是自由主义 者的主要敌人,它自然不太可能作为新建的欧洲文明的基础。 欧盟也许是当今文明国家之间丰富互动的最好例子。一方面,欧洲民族主义直接促成了欧 盟的成立。这是一次超越民族认同、走向政治理性的尝试。起初,这种新形式的政治理性被视 为普遍自由主义。但不久,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任何政治单元可以建立在严格的普遍原则之上。 多年来,欧盟毫不意外地一直在强调其特殊性:欧洲的价值观而不是所谓“普世价值”在 将二十多个国家(可能包括乌克兰)团结在一起的艰难任务中扮演了黏合剂的角色。其结果是 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同的第三条道路。 欧盟基于一系列原则建立,并且不再认为这些价值观是普世性的。欧洲的价值观是欧洲自 己的探索:在明知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一幅独特而繁荣的文明图景指引它选择了这条特殊 36 文明的回归 专 道路。 题 托马斯 · 曼(Thomas Mann)在二战最黑暗的时刻写道,冲突最终是在自然、本能、血缘、 无意识之间的互动—一方面是生命原始的自发性,另一方面则是与理性和文明的对立。 Focus 今天,我们需要从血缘和民族的原始无意识里屹立起来,走向未来的文明国家。 作者系葡萄牙欧洲事务部前部长、咨询公司 Flint Global 高级顾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 译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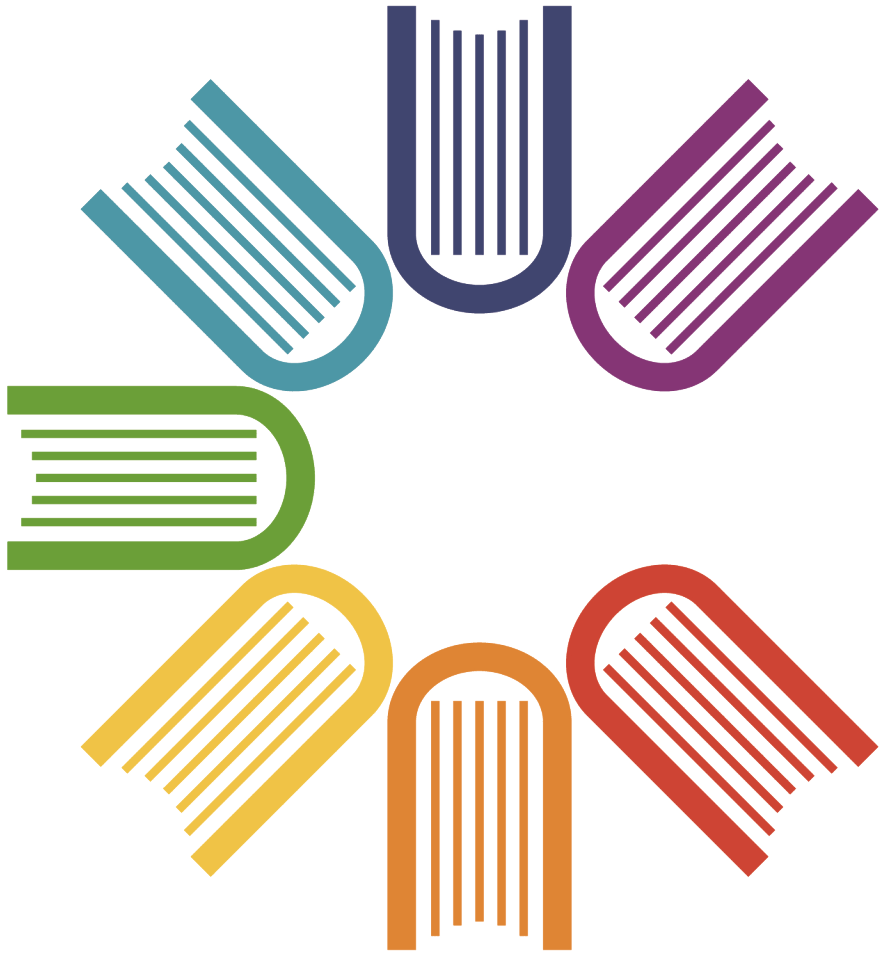
 布鲁诺·马塞斯:文明的回归.pdf
布鲁诺·马塞斯:文明的回归.pdf



